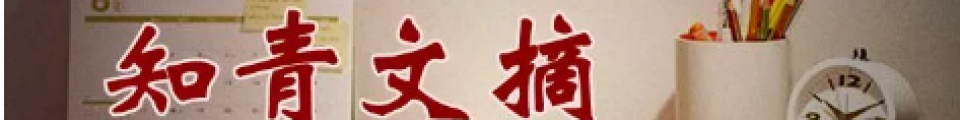路遥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在毕业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我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的这部巨作以及系列创作中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实践,对一代年轻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他在45岁就英年早逝,身后却连续获得了两项殊荣:2018年12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评为“改革先锋”;2019年9月25日被中宣部等部委评为“最美奋斗者”。今年是建党百年华诞,对于路遥这个老党员来说,如若假以天年,“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一定会挂在他的胸前!
路遥曾经为我们的母校延安大学题词:“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延安大学的经历,在他的人生中举足轻重,他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在大学期间就初露端倪,作为老同学,从遥远的记忆中采撷几个片段,权且作为对他的纪念。

1975年路遥上延安大学时在延安纪念馆前留影 谷溪 摄
初识路遥,是在 1973 年延安大学 9 月 7 日正式开学后一周左右。我们延安大学中文系 73 级的同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还收到因有任务提前一个月报到的通知。那是8月初,我没来得及回北京,当时是姐姐送我来学校的,我们背着插队时用的被褥,急急忙忙从农村直接赶到学校,报到时才得知任务是为诗歌集《延安颂》搜集材料。我们是延安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们班又是提前入校,当时女生基本都来了,男生来了一些,其他系都没来,学校空荡荡的。在大家已经混得有些熟了以后,路遥才来,似乎是一个老单位来了位新人。
我是在延安志丹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因为父母在“文革”中被批斗,一直没有招工、招干的机会,当同学们差不多都离开农村的时候,让我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全国高考。当时北京医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来招生的于老师(后任北京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同情我们姐俩的境遇,让北京的同事去我父亲单位讨来了“大人的问题不影响孩子上大学”的一句承诺。姐姐的问题先行解决后,在延安地区招生办调剂名额时,我被延安大学补录,据说延大的老师表示:北医敢要她姐,我们就敢要她。这句话让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多么感谢那一段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多么感谢在关键时刻遇到了北医和延大、志丹县和延安地区招生办的善良的老师们!

1974年8月大学学习期间的许卫在延安大桥留影
可能是这样一段相似的经历,与陌生的路遥刚一见面就拉近了距离。记得他那天是在晚自习的时候第一次踏进教室的门,班上的同学大多数都已报到,空座位寥寥无几,他径直走到了我前面的座位上坐定,不久就扭头朝向我,自来熟地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低沉的嗓音介绍自己的名字叫王路遥,因了他开初的自我介绍,我自始至终都是这样连名带姓地称呼他,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路遥个子本来不高,因为壮实,所以更不显个儿。他无论站姿还是坐姿,总是向左侧微微仰着头,右侧的嘴角轻轻上扬,眼睛不大,可能因为近视而略略眯起,这一切让他永远带着一丝看透一切的微表情。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虽然很多话听不懂,但是我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一幕幕场景:白衣少年独自流亡在深山沟,少年得志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政审差点通不过,结局和我一样:被延大收留。我后来得知,他所在的延川县,出了不少知青名人,大多数是他的好朋友,他主动坐在我前边的位子,除了空位子不多的原因,也是他愿意接近北京知青的善意表现。
我们的教室在小教楼的二楼,是个小教室,30个学员一共6行座位,我们中间的两行座位自然形成班里的第二学习小组。在我们小组里有支部书记张子刚,有后来选为班长的路遥,还有我的同桌刘国芳,路遥的同桌刘平安,以及王志强、齐义、白凤武、王广彦、拓发明、李世平,我被推举为组长。分在一个组,和路遥的接触无形中多了起来,各种有关他的传闻也飘进了耳朵里,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他的诗作,他的组织领导能力等等。
我是文革前的老初一,虽然在插队时读了些书,还给大队办过油印小报,但是以这点底子读大学还是没底气。一来延大,人就进入了海绵状态,我发誓要把过去没有读过的名著都读一遍。延大的老师都非常平易近人,他们经常来学生宿舍随意交谈,启发我们多读代表作。因为借书证迟迟没办下来,想看的书看不到,我就去找文艺理论包永新老师,请他在图书馆工作的爱人段芝霞老师帮助借书。在包老师以及其他老师的耐心辅导下,我按照推荐书单一本本地借着看,记得有一次我想借《堂吉诃德》,却被告知路遥已经抢先一步拿走了,我才知道,写作了得的路遥也在加油充电。我们二组有时候在男生宿舍开讨论会,路遥的床上常常堆着很多书,也证明了这一点。
路遥的读书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他读书速度很快,但是重点书籍反复诵读,重点句子能够背下来,有的书甚至全本都可以复述下来。他常常在同学面前毫无表情地用毫无起伏的语调大段地背诵名句甚至名段,宛如一个用功的中学生。他推崇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名句“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柳青《创业史》的名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在路遥的影响下,这些催人奋进、含义隽永的警句,很多同学都会背,我还把它们工工整整地抄在了精致的本子上保存至今,当作自己的人生指南。应该说,我们班正能量的班风,与这些细节呈正相关。但对于路遥,这么说他就太肤浅了。他自小就挣扎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太多艰难困苦,忍受了太多挫折屈辱,名言警句不仅仅激励意志,更能引导人生思考的深度, 锻造本质上把握生活的能力。说他喜欢背警句,不如说他喜欢深度研究生活,这不仅反映了路遥在大学时代的读书倾向,还可以看出他的创作端倪和发展路径。熟悉路遥的人都会发现,他之后创作的小说无论反映了多么深重的苦难,都会闪耀着希望之光 , 无论是多么平凡的故事,常常穿插一些富有哲理的领悟。路遥的作品呈现出比较突出的理性光芒和思辨色彩,他的内心深处崇尚的是严肃文学,追求的是揭示生活和历史的深刻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路遥写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了解逐步加深,特别是当他提出自编自演《我们生活在杨家岭》诗歌大联唱节目后,我简直惊呆了,全部歌词和朗诵词要自己写?!不仅写出来还要演出来?!路遥叫上了白正明和我,在女生宿舍旁边的 22 号空窑洞(第二年是中文74 级的女生宿舍)里摆上了几套课桌椅,正式挑灯夜战。我和白正明面面相觑,无从下手,给暖壶打开水、给杯子倒水、盯着稿纸作沉思状。只有路遥神情笃定地一手拿烟,一手拿笔地写起来。先定题目,路遥率先提出“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大家顿时眼睛一亮:我们延安大学,特别是位于延大东南角的我们的教室和宿舍,确实和党中央曾经的所在地杨家岭仅一墙之隔,这是何其荣幸和荣耀!这个题目透着喜悦,透着自豪,似乎可以触摸到那激动幸福的心跳!接下来先定下内容和结构,之后一步步进展,路遥不时和我们商量用什么词。那天熬到凌晨2、3 点钟,路遥宣布解散。后来邀请支部书记张子刚参加了创作小组。这样连续地写了一周左右。可以说,诗歌联唱的大部分内容是路遥完成的,作为我,虽然做了些誊抄的秘书工作,也从中初步学习了诗歌的创作过程。之后,歌词谱曲、组织大家排练、借服装……1974 年元旦,中文73 全班同学身着工农兵服装,满怀豪情地唱响了诗歌大联唱《我们生活在杨家岭》,轰动了整个延大校园。
路遥思路开阔敢想敢干,是个干大事的人,他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涌现出来。但是他能够办成大事,绝不仅仅是能干,更是肯干,他做每一件事都是脚踏实地、耐心细致地一点点落实。比如同学们在教室排练《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可能是同学之间磨合得不够,很多同学自身也缺乏唱歌技巧,大家总也唱不齐,甚至发出一些怪怪的声音。我们在楼上唱,他就跑到楼下听,听一会儿就跑上来反馈,指导指导,之后再跑下去听,气喘吁吁,反复再三,不厌其烦。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1975 年10月,中文系组织 73、74 两级学生去当时的学大寨先进典型吴堡县采风,筹备编一本吴堡新民歌选,路遥是总编辑。当时采取的是海选方式,先下到农村基层搜集农民诗歌的原创,然后再分配到各组精选,当时由我负责给各组分发原稿。由于一些原稿比较粗糙,为了节约时间,减少无用功,我先进行了初筛,事后才向他汇报。路遥听了很不放心,本来习惯于微眯的眼睛睁圆了,充满疑问地盯着我,他那是生怕有所遗漏,我只好返身回去把初筛淘汰的所有诗作都拿过去给他过目,他细细翻看了一遍才放心地点点头。虽然如此,我之后再也不敢擅自做主了。他的这份专注和认真,表明了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在他以后的创作道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种责任感又何尝不是他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的体现!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印证这一点。因为是北京人,开学后我就被推荐为中文73级的校广播室广播员。有一天正逢我值班,可是感冒了,嗓子特别哑,我急急忙忙跑到广播室请假,恰巧其他广播员在那一天都无法通知到,我只好被硬拽着哑哑地广播了几句。走出广播室,正看到路遥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他远远地朝我喊着什么,走近了才听出他在恼怒我明知嗓子哑了还要广播,不负责任!我刚要张嘴申辩,看到他那张愤怒的脸和劈头盖脑的责备,真想地上找个缝儿钻进去。路遥就是这么一个对集体的事情热忱较真的人!
说起来,当年的延大,中文系最能够创造热点。动员全系师生之力开展拉网式筛选,派出各个小组去各地较大的图书馆,查阅解放前后的书籍报刊,誊抄搜集,并予以精选。歌颂延安时期革命历程的诗歌集《延安颂》(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2月出版)和歌颂毛主席的诗歌集《红太阳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8月出版),都是这样编辑而成,挽救了历史上很多珍贵的资料。《吴堡民歌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6年10月出版)则是海选农民诗歌原创。短短三年时间内,中文系就在省级和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三本书,每本书都是重大题材,时代主旋律,不但耗时耗工,而且承担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其所创建的平台培养和发挥了能人的才干,提升了学生的学识和能力,这在当时的高校确实是凤毛麟角。巧合的是,这三本书都是诗歌集,对于路遥来说似乎是正中下怀。入学前曾经写过诗歌,编辑过延川诗刊《山花》的路遥,当时对诗歌情有独钟。1973 年秋,配合着系里的教学要求,他给大家布置了至少写一首诗的任务,由此编出了一本刊印的学生诗集《烈火熊熊》,在学校名噪一时。路遥组织的中文系集体演出节目,包括入校第一年和最后一年的新年联欢会节目,也都是诗歌。上面说过入校第一年路遥组织的集体节目是《我们生活在杨家岭》诗歌联唱,他亲自编写歌词和朗诵词。中文系最后一次集体节目,是毕业那年即 1976 年元旦新年联欢会上,集中全中文系 73、74、75 三个年级的学生以及学校年轻教师、学校乐队,共同演出的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音乐史诗《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也是诗歌联唱的形式,但是规模更加宏大。这两次学生自主发起组织,系领导全力支持的大动作,在延大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
中文系所创造的热点,都是诗歌。是诗歌这种简短有力的形式适合于表达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而诗歌又恰恰是那个时段路遥的最爱?有道理,但是好像不尽然。
据我们班同学王志强回忆,最后一年的节目,路遥原本是计划集体唱《黄河大合唱》的,因为学校乐队的规模不够,乐器的品种太少,后来选择了《长征组歌》。这些原因确实存在,但是比较表面,据我所知,真正内在的原因另有其他。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一部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记录了1934 年8月至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这部根据著名的将军诗人萧华的长篇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编排的声乐套曲,在1964年10月编创完成,1965年8月1日由北京战友歌舞团首次在北京公演,获得巨大成功。到了文化大革命,随着萧华和其他老干部的纷纷倒台,《长征组歌》也被打入冷宫。但是就在仍属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5 年,在全国仅有八个样板戏的凋零岁月,居然传来了中央军委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复演《长征组歌》的决定。这绝对是一个信号!每天习惯抱着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的我,听到这条新闻心里一机灵!
种种小道消息在人们中间隐秘地流传着:邓小平在 1975年初刚刚主持军委工作,就决定复排《长征组歌》,不但要公演,还要拍电视、拍电影。随之在1975年6月整顿工作全面铺开,一批老干部包括萧华也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毛主席对四人帮进行了点名批评,经过修改、加工,复排后的《长征组歌》,10 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再次公演,连演45场,场场爆满……
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长征组歌》复排复演具有象征意义,它是唤醒沉睡大地的晨曦,它是划破黑暗夜空的信号弹。
那天,关于《长征组歌》复排,我和路遥交流了消息,他神情兴奋,坚定地说:我们也唱《长征组歌》!内中的含义呼之欲出:与复排复演遥相呼应,参加反击战!致敬老前辈!
经过积极的准备,中文系全系上下投入了极大的力量排练《长征组歌》,大家都拿着同学自己刻印的厚厚的歌本,合唱的中文系同学和学校的部分年轻教师晚上就去大礼堂练歌;学校乐队的同学抱着乐器全力配合;中文系教现代汉语的刘育林老师执棒指挥;数学系熊道统老师的爱人於瑞文老师是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的高材生,担任女声领唱,我们班支部书记张子刚在《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后继续担任男声领唱;我和中文 74 级的男生陈泽顺负责朗诵。我当时每天晚上坐在宿舍门口,抱着收音机一字一句地反复收听《长征组歌》,一边听一边小声地模仿。有一次晚上8:00 多了,路遥从门口路过,说是去大礼堂练歌。之前路遥曾经借调到《陕西文艺》当编辑,现在他回来了,晚上只要有空他就直奔大礼堂,不仅参加排练,还随时配合着掌握质量和进度。
演出那天,我们众多的演员和乐团的同学们穿着整齐的绿军装,在舞台上齐刷刷地站成四排,挺拔帅气的指挥刘育林老师举着指挥棒站在前面,随着荡气回肠的音乐声响起,一台英雄史诗以其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征服了观众们的心。
演出在继续,而我完成全部朗诵回到座位上时,坐在场下观看的老师们齐声夸赞:不错,很好!我却以出人意料的挑衅方式说:谁敢说不好!记得一位老师表情微微一怔。其实,我还深陷在那种秘而不宣的战斗豪情之中不能自拔,能够和同学们以我们所能运用的方式参加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值得终生铭记!
也许有些同学不知道,在我们毕业之后若干年的新年联欢中,各届中文系师生都把《长征组歌》作为新年联欢会的保留节目,一届一届地传唱下去,成为一个光荣传统。之后问起来,多数中文系新同学都不知道这是路遥发起并组织的大手笔。
后来听说,北京战友歌舞团被指责为老家伙翻案 , 抵制八个样板戏。到1975年底,邓小平再次变成了批判对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敬爱的周总理在1975年底病重时还曾要求观看《长征组歌》的录像,不久在1976年初去世。很快,天安门事件发生了。
形势越来越严重,小道消息越传越盛。 1976年春的一天,我和路遥一起去老师那里谈毕业实习的事,走在半路上他拿出一个精致的大本递给我看,我狐疑地打开一看,原来是期盼已久的“天安门诗抄”!据说是一个记者刚从北京带回来。当下我就和路遥说好了先借给我抄几首。收好了本子,路遥突然开玩笑说,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以后到法庭我也不承认,就说是你说的。我也笑着回驳:我就对法官说你就是造谣公司的。嬉笑之间体现出的是忧心忡忡。那时候正直的中国人都是忧国忧民之士,路遥更甚,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就是因为他时刻关注社会的变化,随时把握时代的脉搏。在之后的小说创作中,他把这一阶段的国家大事作为人物命运的底色,挖掘出草根人物的生存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相依共存的关系。
我们中文73 级1976年8月毕业,接着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没有几年,路遥的一部部厚重的作品陆续问世了,获奖了,他的作品活跃在中午时分的小说连续广播时间里,在热播的广播剧、电视剧和电影里…… 路遥出名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后来听到《路遥传》以及同学们的回忆,才知道路遥生命的最后历程走得异常艰难,不禁泪目。我才意识到,路遥出于自尊没有向同学们求援,而自己在忙着千头万绪的时候,也未能给予出自同学的应有的关心,老同学们如果都伸出援手,路遥还会走得那么早吗?
在校期间就听同学们传说,路遥因为天天熬夜透支了健康,曾经在洗澡时晕倒。其实这种日夜颠倒、体力不支,在后来居然成了他的日常。除了病痛,除了经济原因,人们普遍感觉他后来所制定的计划:“40岁前写出人生最重要的作品”,确实太操之过急了。忘记是哪一年了,记得有一次他沉思良久之后突然问我:我想出名,不仅在中国出名,还要在世界上出名,你会有看法吗?我心中蓦地一惊!原来他有这样高远的宏大志向!当年丁玲的“不鸣则已一鸣则惊人”的观点在文革中被批判,但我却认为:不想出名的作家不是好作家,李白的千古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代表了多少中华男儿胸中的豪迈!我的回答自然是“不会”。也许这就是他把自己逼得这么急、这么苦的主要动力?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这个画面:吴堡,黄河桥头,奔腾咆哮的黄河水一往无前,滚滚流逝,河边有一行摩崖石刻“逝者如斯夫”,路遥在此伫立良久,很有触动的样子。这幅曾经的画面,真是路遥一生的写照啊!他珍惜时间胜过珍惜健康,他的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如同这决绝的黄河之水,不舍昼夜地向前疾驰,忘我地疾驰……
我所认识的那么有志向、那么有才华、那么有思想、那么有内涵、那么有前途的作家路遥,就这么轻易地走了,留下永远的遗憾,令人不禁扼腕长叹!
可以告慰路遥的是,今年,在建党百年纪念活动期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大学时代》一书的发行仪式和首发座谈会在延安大学举行,填补了路遥研究的空白,路遥奋斗的足迹,再一次载入史册,我们73、74级的同学们都参与了编写,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路遥,安息吧!
写于2019.8.15
定稿 2021.7.15
(文稿编辑修定:冯军)
作者简介
许卫,北京知青,1969年2月赴陕西志丹县向阳沟村插队曾近5年,1973年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1976年毕业留在延安大学任教,1983年调回北京,曾在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校任教,现已退休。
联系电话:1551002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