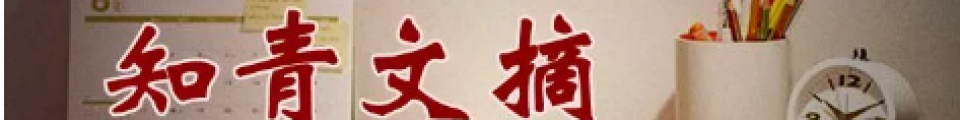我的马倌生涯(一)
——谨以此文纪念赴内蒙古牧区插队五十周年
1968年8月17日我和孙海麟等16位同学一起离开天津南开中学,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公社插队落户。克尔伦公社在满洲里西南大约400华里处,毗邻蒙古是典型的内蒙古牧区。
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蓝天下的羊群、马群、牛群,给人以无限遐想。那时牧民们称我们为“斯和腾扎娄”,简称“斯和腾”,在蒙语中就是知识青年的意思。到公社后我和孙海麟、张永裕、朱哲通三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额日和图大队。特别是在南开中学获得的知识与素质训练使得我们的蒙语学习、放牧技术和组织能力很快得到提高,并得到了牧民、大队与公社领导的肯定。
1969年9月起我被公社和大队领导任命为额日和图大队会计,清理了额队多年的糊涂账,为大队的经济发展梳理出脉络,奠定了基础。
1972年9月,我被选调到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进修班学习,离开了克尔伦。至今我已从事数学工作四十多年了,但我却曾是内蒙古牧区的一个称职的马倌。马倌通常要负责任、技术好的人才能胜任。那时额队的马群有八百多匹马,通常有两到三个马倌负责放牧。大马倌负责白天看管马群、选择草场,二马倌负责下夜、在夜间看护马群、防止马匹走失和防止狼群的攻击。
1969年秋大队任命三十多岁的莫胡杰任大马倌,我和另一个蒙古族青年巴图西日任二马倌。1971年秋我又被大队任命为大马倌。马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当时我们大队的马群有十二匹儿马(公马)它们各自带领着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由若干匹母马们、骟马和许多幼马组成。儿马通常会照顾它的家庭成员,遇到风雪或狼群时把它们圈到一起。幼马长到四五岁儿马会把它逐出家庭,让它自立。马倌就是根据这些马群家庭的情况和马匹的颜色来给每匹马起名字,记住它们。
每天早晨马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点马群以防马匹丢失。马倌骑着马在马群中转一圈,必须能马上发现走失的任何一匹马,说出它的名字和特征,然后尽快把它找回来。除了认马以外,马倌还有许多技术要掌握,大至选择草场,小至打各种拴马的绳扣。其中最基本的技术之一是套马。套马所用的套马杆是一根长约四米多的木杆,将一根皮条两端系在套马杆最前面约一米处形成一个长约四米多的木杆,将一根皮条两端系在套马杆最前面约一米处形成一个套马圈。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套马的要领:首先,马倌双手前后持套马杆,同时用左手持马缰绳控制所骑的马的前进方向;然后从左边追上要套的马同时用左手持马缰绳控制所骑的马的前进方向;然后从左边追上要套的马时,将套马杆上的皮条向左甩,套在马脖子上;同时人坐到自己马鞍后面,鞍后面(这就像从自行车的座位上坐到后货架上一样)然后借助坐骑的力量用力拉住。此时其他人就可以把马抓住。如果被套的马十分不老实,还需要把马皮条准确地套在马的两只耳朵的后面,勒住它的脖子。再不老实的马这样套住后,手上稍稍用劲就可以把马拽住。由于坐骑和想套的马都在高速奔跑中,被追的马总在不断变换方向,逃避追捕,这就需要保持平衡中实现这一系列操作技巧,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1969年秋我到马群后,莫胡杰给我演示了一下如何套马,就让我试试。第一次套马,我骑着马由左边追近前面在右边跑的马时,最方便的套法是将套马杆上的皮条向右甩,套在马脖子上。但我这样套上马后才发现无法将套马杆上的皮条向右甩,套在马脖子上。但我这样套上马后才发现无法抬高套马杆的位置,套马皮条一下滑到了马的胸上。被套住的马受了惊拼命向前蹿。无论怎么用根本拉不住它,我反而被带离了马鞍,一下趴到了坐骑的脖子上。然后既无法退回到马鞍子上,也无法继续保持平衡,只好一咬牙从马脖子上摔了下去。套马杆也被前面的马带走了好远,我从地上站起来捡回了套马杆,重新骑上莫胡杰帮我套住的坐骑,又开始了新的尝试。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掌握了套马的技巧。
驯马是放马的又一个重要技术,是人与生个子马的较量。生个子马是牧民们对从未被骑过的马的称呼。这种马一被人骑上就会不断尥蹶子,不把骑手扔下来,决不罢休。好的骑手在马背上能够很好地掌握平衡,不仅不被尥下来,还要驯服马教会马做各种动作。那时我的骑马技术已较好,一般的生个子马尥蹶子扔不下我来,很得牧民们的称赞。(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新右旗克尔伦公社天津知青(作于2006年修改于2018年)
我的马倌生涯(二) 龙以明
——谨以此文纪念赴内蒙古牧区插队五十周年
有一次莫胡杰和我与邻近的赛汗塔拉公社的马倌们一起聊天,得知赛汗塔拉的马群中有一匹很厉害的生个子枣红马,几个试图骑上它的人都被生个子枣红马尥蹶子扔了下来,当时没人再敢骑它。莫胡杰告诉他们我骑马的技术很好,可以骑。那时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跃跃欲试。赛汗塔拉的马倌们很快就到马群把那匹枣红马套住,带到公社边上。听说克尔伦的“斯格腾”要骑这匹枣红马,很快那里就围上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许多人来看热闹。
莫胡杰和几个马倌按住枣红马的头,给它套上了马鞍。我骑上马后,莫胡杰高声嘱咐我小心,然后让几个人同时松开手。这枣红马果然性情刚烈,桀骜不驯,不停地又蹦又跳,低着头拼命尥蹶子,一心想把我从它背上摔下来。其实骑马中也有物理知识,这时就用上了——要想不不被马尥蹶子扔下来必须随时注意保持身体重心的平衡,身体应该尽量向后仰,同时要放松,随着马的跳跃不断地调整身体姿态保持平衡。枣红马一边尥蹶子,我一边注意保持身体平衡,并一边用马棒不断打它。直到它跳累了,我一提马缰,枣红马一溜烟向公社外面跑去,一直跑了四五里地我勒住马缰让它转回头慢慢地跑回公社。
马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一次被你驯服以后,你再套住它骑上的时候,它认得是你再也不会闹。这一下,我这个克尔伦的斯格腾马倌在赛汗塔拉马倌中出了名。做马倌的技术要求很高,在牧区是很受尊敬的工作,同时又是具有相当危险性的工作。但我接手当马倌时并未意识到这点,而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1969年的年的11月初,天气已经很冷,夜里已到零下二十多度,克尔伦河已经完全封冻。我们的马群在河套里停留了两天。河面上冰很厚,冰面上露出很多芦苇,马很爱吃。那天早晨大约八点多钟,我和莫胡杰吃过早饭,一起骑着马到马群巡查、换马。马倌一般每天换骑两次马,白天一匹,夜间一匹。
莫胡杰那天心血来潮,要我去套一匹高大的棕黑马。而这匹马的顽劣出了名,我刚刚靠近它,它就在冰河面上狂奔起来,我骑着马像往常一样很快跟了上去。我的套马圈刚刚套上棕黑马的脖子,它突然一个左转弯,我骑的马习惯性地跟着就转了过去。由于冰面太滑,速度又很快,我只感到我骑的马一滑,就连人带马摔倒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慢慢睁开了眼,觉得头很疼,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我躺在克尔伦河的冰面上,向上看见周围的马很多,但又好像都离我很远很远。又过了一阵,好像从很远的天边慢慢来了一辆敖登车,就是有两个橡胶轮胎可以坐两个人的那种轻便马拉车。车上下来一个人好像在与莫胡杰说话,但我听不见他们说的任何声音。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人上了车,又向天边的方向离开了。又过了好久我慢慢听见了莫胡杰叫我的声音。我坐起身,想起了我的套马杆还应套在棕黑马的脖子上。莫胡杰帮我套住了我的坐骑,我又歇了一会儿,然后骑上马,我们一起在棕黑马附近的冰面上找到了我的套马杆。
莫胡杰好像在跟我说什么,但我仍完全没有什么反应我们一起慢慢走回到我们放马的小蒙古包坐下来。这时慢慢想起了事情的大概过程。莫胡杰告诉我,我摔到冰面上后,曾经试图抬起身几次,挣扎起了三次,再也没能起来。我逐渐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忽然想起了远在北京的年老的爸爸和妈妈,眼泪流了下来。莫胡杰这时才高兴地说,能哭了就好。后来我才发现,我的手表的玻璃表蒙子已摔得全没了踪影,表盘也完全凹了下去。也许是手表挽救了我的胳臂,所幸胳臂腿都没有受伤。但我的头还是很疼。随后,莫胡杰又陪我骑马去找一位蒙医大夫看了,他说是脑震荡,但也没有什么药,只能给我做了一阵头部按摩,然后让我回去休息。又过了几天,我才逐渐完全恢复。所幸我那次被摔得还不算厉害,后来还能学懂高等数学。不过那以后我再不敢在冰面上套马了。
新巴尔虎右旗坐落在大兴安岭西面。冬天夜间的气温要到零下四十摄氏度,白天也有零下二十多度。平常我们都是全副武装:身穿皮蒙古袍、皮裤,手戴皮手套,头戴皮帽,脚蹬毡靴,草原上叫作毡疙瘩。
1969年秋冬时,我是二马倌,晚上六七点钟左右天黑时离开我们的蒙古包去照看马群,要到第二天七点多钟天亮后才能回来。由于夜里太冷,我们都在皮蒙古袍外面再套上一件皮马褂御寒。就是这样也严寒。每隔半小时左右,就需要牵着自己的马在草原上步行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直到身体暖和了才能再歇一会儿。
马倌套马时由于需要用力抓住套马杆来制服不老实的马,为防止手滑不能戴手套。有一次,早晨北风呼啸,气温骤降我到马群套马。由于套马时间较长手不断用力,又不能戴手套,双手手指都被冻得没有了任何血色。回到蒙古包后,手开始剧痛起来。莫胡杰看后赶快倒了一大碗白酒,让我把手指浸在里面泡。这时的双手真像是用许多针扎在上面一样疼。泡了大约半小时,手指的颜色才慢慢缓了上来,最后没有发生冻伤。(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新右旗克尔伦公社天津知青(作于2006年修改于2018年)
我的马倌生涯(三) 龙以明
——谨以此文纪念赴内蒙古牧区插队五十周年
俗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这还真是马的天性。白天的许多时间马群都在站着睡觉,到了傍晚开始吃草,夜间有时也小睡一下,但大部分时间在吃草,一直到天亮。因为吃草,马群通常散成了面积很大的一片。那时狼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十多只狼一起跑过。狼通常是在夜里向弱小的马匹发起攻击,不过狼似乎很怕人,我从未听说过狼攻击人的事。马倌下夜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时吆喝几声把狼吓跑。
有一次夜里暴风雪,我把马群赶进一个大山谷里吃草,然后在谷口坐下来歇息背向谷外,看守着山谷里的马群。雪下得很大一会儿就像给我穿上了一件白斗篷。我忽然听到身后似乎有什么响动,于是猛然回过身来,发现身后不远处蹲着一只灰狼,它大概也正在揣摩这个一身白雪的是什么东西。我一惊,一面猛地站起身来挥舞着套马杆,一面高喊。那狼大概也受了惊吓扭转身一溜烟地跑走了。
我在中学时喜欢下国际象棋。内蒙古牧区流行蒙古棋,它的下法与国际象棋相同,只是棋子做成马牛羊骆驼的样子而已。冬季马群离开公社出去游牧的几个月中我们与外界隔离,完全没有信件报纸,下棋是一个重要的消遣。那年快到春天的时候,新巴尔虎右旗派了一个畜牧巡视员来克尔伦河北看望牧民。十分遗憾现在我已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还记得他的儿子曾因吸烟引发克尔伦草原大火。他五十多岁,稍有一点驼背和蔼可亲,住在我们的马群包里。他与我很谈得来。他也是个十分喜欢下棋的棋迷。出于尊敬,我与他下棋都让他一些,这样我们的对局中都互有输赢。晚上他和我们几个马倌聊天通常聊到很晚。一次聊到下棋他颇有得意的意思。
那年冬季克尔伦队的马群与我们的马群混在一起放牧,马群包也搭在一起。克队的大马倌奥斯尔了解我们两人下棋实力对比,要与巡视员开玩笑,就力邀我与巡视员连下五十盘棋而保证不输一盘给他。莫胡杰等人于是也马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第二天不需要我干活,他们把所有事情包下来,专门看我们两人下棋。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就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对局。那些盘棋我都下得很仔细,一般都在三五分钟内就可以赢下一局。莫胡杰他们一面给我们烧茶喝,一面谈笑风生,鼓励我们对局的双方。
巡视员不时站起来到马群包外面活动一下疲劳的筋骨,放放风。一直下到第三十六盘时,我一不小心被他赢了一局,对局才告结束。大家都风趣地说总算下完了。这以后我和巡视员成了很好的朋友。
马倌生涯就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充满了挑战与欢乐,也充满了艰苦和危险。离开牧区三十年后的2002年9月,我做为孙海麟带领的天津市政府代表团和天津市知识青年代表团中的一员又回到新巴尔虎右旗看望乡亲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牧区发生的巨大变化。牧区的领导和乡亲们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热血青年们。新巴尔虎右旗还修建了“思歌腾广场”(即“知识青年广场‘’)来纪念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对牧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天津市政府代表团赠给新巴尔虎右旗五十台计算机,帮助旗中学建立计算机实验室。我们一行又专程回到克尔伦苏木看望乡亲们。天津市政府代表团向乡政府赠送了背投电视。乡领导和牧民们专门举行了仪式并且举行了摔跤和赛马比赛热烈欢迎我们回到克尔伦。十分遗憾的是,那时额队原来的书记沙木苏荣、两任大队长边巴和阿迪亚、副队长图门巴雅尔和莫胡杰等老朋友都已逝世。那几天中我见到了许多朋友。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大家都对牧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进一步发展和以后更加美好的蓝图充满了信心。
回首那几年在克尔伦的生活,我为牧区的发展兢兢业业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也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了解了中国最底层的乡村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五十年来,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自己则有幸走上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道路,并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很高兴以此文来纪念我们一行十七名同学到牧区插队五十周年。(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新右旗克尔伦公社天津知青(作于2006年修改于2018年)
(2006年5月7日初稿,2018年8月17日修订)
龙以明 南开中学1967届高二2班
龙以明简介——
1967届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二2班校友
1968年8月下乡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牧区。
1972年9月被选调到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进修班学习。
1981年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
198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数学学院院长、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数学会理事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数学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
2000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3年当选美国数学会首批会士。现任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天津南开中学校友理事会理事长。南开中学校友理事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