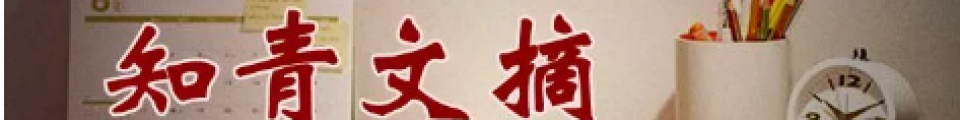我是1970年4月去云南军垦上山下乡的。记得当年从上海出发的时候,在火车上有几位同学闲得无聊的时候,躲到厕所间旁边偷偷摸摸地拿出香烟抽了起来。一股烟味袭来,整个车厢里顿时就弥漫着浓浓的烟味。
见此情景我跑过去站批评他们:怎么可以抽烟啊,这是流氓阿飞的行为!
没有料到这几位朋友哈哈一笑:管你什么事情啊,我们长大了,抽点烟是正常的!
当时护送我们去上山下乡的老师见状立刻把他们的香烟收缴了,还大声呵斥道:不许抽烟!你们都是去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哪能学会这些不良嗜好?再让我发现立即批斗!
没用啊。我们到了昆明休息了三天,这几位哥们只要有机会就聚在一起抽烟。后来从昆明出发前往西双版纳的路途中,他们居然大大方方地抽起烟来。
一年后我发现连队里大多数的男同学都学会了抽烟,我是极少数坚持不抽烟的人。
雨季天的云南,一会儿是一场瓢泼大雨,一会儿是骄阳高照。下雨的时候,我们在山上无处躲雨。戴着斗笠站在雨中瑟瑟发抖,等待大雨过去后继续干活。
那天,连队的副指导员老殷站在我的身旁,雨中的他掏出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着一根,雨不停他的烟在嘴里永远地叼着。突然他看见愣在一旁的我,立即掏出一根烟递给我说,抽一根,解解闷。
我接过香烟点燃后抽了一口,紧接着是一阵猛烈的咳嗽。我的天啊,这烟真的难抽啊。
不到一年的时间,连队里的男知青们基本都学会了抽烟。特别是每天到了晚上全连开大会的时候,大家都坐在一起抽烟。至于领导上在上面讲些什么,爱听不听的。
那时我们抽的香烟都是2角一包的玉溪牌香烟。较多的人抽的是2角8分一包的金沙江牌子的香烟(相当于当时上海的飞马牌香烟)。比较奢侈的是春城牌香烟,价格与当年上海的牡丹牌香烟差不多。
连队里有一位男知青,他只要抽烟就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多次尝试抽烟后,他是唯一一位不抽烟的男知青。
记得每次上山干活,这位不抽烟的男知青总是被山上的大蚊子咬得四处红肿。我们大家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感觉。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抽烟的身上有股味,连蚊子都不靠近了。
到了雨季天,河水猛涨把连队通往小镇的桥梁冲垮了。这下苦了我们这些烟瘾人。开始几天还有香烟可抽,接下来几天大家相互照应着节约一些抽烟,到了一个星期后,全连断烟了。
一天我们看见一位老工人坐在家门口抽烟,大家都感觉很好奇。怎么这位老兄还有香烟抽?
第一次看见女知青抽烟是在一个傍晚,那天是星期天。那时的农场在休息日的时候,食堂只供应两餐饭,上午的9点和下午的4点。
那天我们早早地吃过晚饭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我习惯性地端着一个小凳子来到橡胶林地边上看书。当我走进林地的边上时,从不远处传来一股烟味。我赶紧走过去想看个究竟,是谁在休息天躲在这里抽烟?
等我走进的时候心头一愣,怎么是个女人坐在林地里抽烟?从背影上我就能够认识是小莉,她干嘛要在这里抽烟?再说,平日里从来没有看见小莉抽烟啊。
我看见小莉的脸上挂满了泪珠,连忙问道,干啥呀,怎么抽起烟来了?
小莉猛吸了一口烟说道,我的病退被场部卡住了。场长说只要他当道,一个知青都不放!
回到家我把香烟作为礼物送给了父亲。他乐呵呵地说,第一次看见外地有这么多的香烟。
那时,我们云南的知青开始大返城了。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到北京去请 愿的知青们的消息。生产队里早就冷冷清清了,大家都不干活了,等着可以回家的消息。
除夕那晚,我们留守在队里的几个知青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喝着聊着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抗日救亡歌曲:
“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堂?”
那晚,我们没睡。大家围坐在一起闷头抽烟,地上积满了烟头,整个屋子里烟雾腾腾。等到了天亮得时候,口袋里得烟抽完了。一位朋友说,完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整个农耕民俗博物馆占地660余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1800平米,博物馆于2016年9月12日正式挂牌开馆运行,它是滇域农耕文化馆、记忆工坊、知青云南记忆馆、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筹)(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综合实训基地)三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共分三层:负一层序厅主要展示的是知青云南记忆馆;二层为滇域农耕文化馆,三层为二十世纪初法国农村生活景象老照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