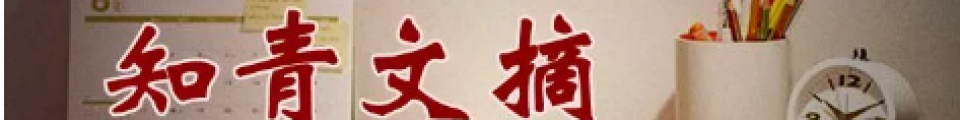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肇始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潮水般涌回城市。
本文试图厘清:知青返城大潮为何没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却发生在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
1971年3月6日。重庆二中初二女生李玉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那天,菜园坝火车站,至少有上千个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哭成了泪人。”李是泪人之一,“记得我走在队伍前面,怀里还捧着《毛主席去安源》”。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
“(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
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事出有因,缘于当时极左,上海要凑足输出“百万知青”的壮举,竟拉农村青年凑数。上海阿乡大多勤劳克俭,宽厚谨慎,组成了兵团连、排、班的一线骨干。
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兵团好几次惊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的大械斗,就由重庆知青发起。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将近30年后,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北上请愿总指挥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现定居重庆,“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10分场(原云南兵团1师1团10营)学校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
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
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问题,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并没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
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据称后来写《棋王》的阿城(当时也是1团10营知青)曾当过丁惠民的高参,丁回答:
“没有这种事,阿城曾当面向我表示他反对请愿活动,怕知青出事”。
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3人核心小组。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余人。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
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通过筹备组表决,丁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丁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30年后,云南省公安厅知情人士坦陈,“钱是我们派人调了包,目的就是不让知青进京,这是当时省委领导下的命令”)。
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3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
这种过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在第一批北上代表闹僵的同时,第二批代表紧急暗渡陈仓。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过了澜沧江,“我是准备死在路上了”。
50余名代表艰难辗转,终于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途中,一些代表喝酒、赌烟,被丁开除。
“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上”,并认为,“邓副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人”。
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
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曾经是八路军359旅旅长、以开荒南泥湾后来又以军垦驻屯闻名的王震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
丁记得王震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
代表们落座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
“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现在南疆前线形势紧张,我们的军队正准备自卫反击,国家需要安定团结,希望你们顾全大局……”
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
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据称部队要排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
电影结束后,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它;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把它建设好,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王副总理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
听说丁惠民有病,王副总理立刻叫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还开了一堆药品。
暖流正在形成,气氛应该是不错的,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打断了一切。
当时,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
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
这个干燥的重庆崽儿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副总理也一下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楞头青对他这样叫?
王震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老将军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楞小子。骂的大意是:你这个缺瓜篼的(湖南话断子绝孙),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离开电影院,丁惠民决定,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其沮丧可想而知。
代表中,包括重庆知青刘先国、涂清亮、刘庭民、刘普选、李长寿、邹盛永、张秀瑛、谢继红、谭德超、黄有志等——他们并不知版纳正在发生逆转。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
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
在6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种种因素促使应尽快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知青问题。
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3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
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
“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省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
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也就在这一天,丁惠民在返滇途中解散了筹备组,并向王副总理致电,就知青的过激行为向国家道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李玉华清楚记得:
“短短几天,整个团场走空了,连队静得可怕!大家丢下武器,抛弃农具。很多人搭乘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运送物资的返程卡车上昆明,由于拥挤过度,发生了好几起翻车事故;也有人拖儿带女,不顾一切地搭车北上”。
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到了昆明,才松了一口气,“就像在做梦,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拍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
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过去时名词。
1980年代初,在国务院知青办起草的知青工作回顾与总结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为解决就业问题,但在文革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回到本文前述的提问: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难道,他们真是外来的种子,一不小心掉进云南雨水丰沛的野地,没受多少作践反倒长成了气候么?
首先在于,去云南的知青心理震荡要大于其他地方。当知青们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来到西南边疆的深山老林,其心理落差,不仅是路途的几千公里,还包括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全部进程。
其跨度涵盖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京、沪等大城市,再到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刀耕火种之地,它对人的心灵震撼若非亲历则无法感知,也促使云南知青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识和思索更为深刻。
其次,云南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4兵团陈赓之旅。这是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雄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云南。
该部有大批官兵于50年代就地转业,创建边疆国营农场,许多老干部保持着优良传统,与知青们朝夕相处,血肉与共,其果敢精神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的个性。
再有,与北大荒和其他插队知青不同,云南知青的劳作成果不是春华秋实的稻菽,而是橡胶树,种下去,能活五六十年!遂成为他们生活的见证与情感维系的纽带。
当上山下乡的大潮将他们抛掷到边疆后,他们无法回避,只能用身体去体验大的苦难和大的欢乐,流大滴的汗、喝大口的酒、掉大滴的泪,一旦梦碎,他们便以另一种方式选择命运。
更重要的是,当时文革形成的政治高压正在消解,政治清明正在恢复,中央对大返城的定调符合民心,这才使云南知青的行为没被扣上帽子。
虽说大返城已40余年了,但如今每年仍有成百上千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他们说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对岁月永久的纪念。
他们年轻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吗?
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他们把握了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
整个农耕民俗博物馆占地660余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1800平米,博物馆于2016年9月12日正式挂牌开馆运行,它是滇域农耕文化馆、记忆工坊、知青云南记忆馆、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筹)(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综合实训基地)三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共分三层:负一层序厅主要展示的是知青云南记忆馆;二层为滇域农耕文化馆,三层为二十世纪初法国农村生活景象老照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