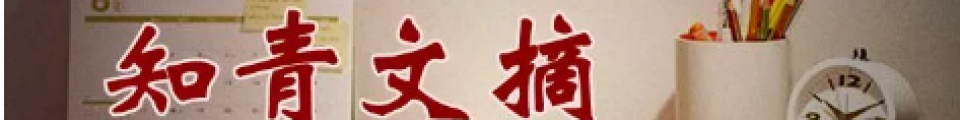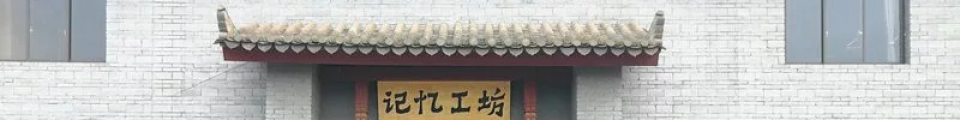关 纯 情 节
潘长旭
关纯,系距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县城约3公里的一傣家人聚居村寨,20世纪70年代初为盈江县学大寨(当时在全国农村的口号是:农业学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示范点,其时该寨强劳力日工分值达一元二角,堪称全县冒尖富寨。承蒙时任盈江县再教育办公室余仕德参谋(余是0297部队派到县里专管知青工作的军人)理解通融,让有志到大寨点写通讯报道的我于1969年秋收后再去找他。这余参谋果然言而有信,秋收后我再去再教育办公室,即得到他让谢姓工作人员开具的,从弄璋区新府乡弄相寨迁至平原区新莲乡关纯寨的“通行证”。
我之所以欲别弄相寨奔关纯寨,缘于三大因素,其一,公元1969年8月1日凌晨突发的一场泥石流灾害,将弄相寨三分之一的良田一夜之间变成一片荒漠。这场灾害,使弄相寨社员(当然包括知青)的工分急剧贬值,至年底结算时,我这个强劳力在分口粮之后,居然倒欠社里五元一角二分(这款项在当时决非属零花钱)。其二,关纯为大寨点,欲在通讯报道写作上有所作为的我在关纯寨可有用武之地,并可以此为基地,为日后的蹦跶做好铺垫。其三,加盟关纯寨收入有保障。其时知青的未来走向根本没定数,就地扎根的概率颇高,有此可观收入垫底,就算蹦跶不了,也能将就混得过去。落脚关纯寨一年后家庭出身欠佳的本人破例应征入伍之事态证明,战略转移至关纯寨,为我明智之选择,关纯寨,乃我之福地矣!
道及在关纯寨的经历,两位关纯寨“编制”以外的人物有必要聊之一二。贴切地讲,这两位人物称为师长更为适宜。两位师长为,县革委会驻关纯寨工作组组长龚维敬、工作组成员刘汉振。说起龚刘二位,可谓各有千秋。龚老师脸庞子、身材均显瘦,一幅文弱书生的样儿。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为其显著特点。曾记得,那时为盈江县大寨点的关纯寨晚间会特多。在会上呢,这龚老师为主讲。讲啥呢,讲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讲全县学关纯,这关纯该咋办?讲学大寨中的好人好事,讲5月1日关秧门势在必行……以龚老师为代表的学大寨工作组号召力之大,凝聚力之强,至今回忆起来,仍令我为之叹服。须知,那时关纯寨社员和知青们从太阳露脸出工至烈日当顶小憩,再一鼓作气干至太阳落山的劳作模式,已成为誉满全县的响当当的“拳头产品”。在这大干苦干氛围熏陶下的我,有两件苦干“作品”值得一提。“作品”之一为,开创了令傣家人为之惊叹的穿着背心堆谷子之先河。要知道,将割倒在地的带杆谷穗用手拢起来,捆起来,继而再担起来,直至登梯将其码上谷堆,为堆谷子的必经程序。因那穗杆对手臂内侧戳得厉害,故堆谷子时,傣家人都好穿上厚实耐磨的长袖衣裳操练。我这人穿戴历来喜欢简洁,加之好出汗,当然更实质性的许是性格使然,居然利索地尝试仅穿件背心裸臂操练堆谷子活计并坚持了下来。“作品”之二为,我在干活之余,写出一篇篇广播稿,在收工后打着赤脚步行3公里直送县广播站“侯广播”处(适逢下雨,则是披着蓑衣前往的)。我以为,这两件“作品”,或为当年“老三届”在广阔天地所创诸多“作品”中不可多得之“孤品”。
当年关纯寨“老知青”在大寨精神鼓舞下那苦干劲头,尚有一情节可作“充填”:为赶在5月1日前“关秧门”,关纯寨的社员、知青们打起火把夜战插秧,夜战中,长相俊俏的当地知青苏桂兰晕倒在水田里……
要说的是,苦干到这般程度,每周三四个晚间的社员大会那是照例要开的。全员齐刷刷到会,是那时社员大会的定型“景观”。只要喇叭一响,五六十号人准是一个不会少全到位的。社员大会的主讲,自然是能操一口流利汉语傣话,口若悬河的龚老师,其诙谐幽默亦不乏严肃话题的演讲,常令傣家人和知青忽而凝神听得津津有味,忽而发出哄堂大笑。
这龚老师,尚有一令我深感惊诧并耐人寻味的“特异功能”——听功。记得有一晚,冒着毛毛细雨打着赤脚往当地知青吴家林住处串门的我,人尚未进得其屋,即听得里头传来一阵熟悉悦耳的声音:“是潘长旭来了!”待我进得屋里头,那吴家林嘴巴张得老大:“龚老师啊,你的耳朵咋听得这么准啊!”龚老师他慢吞吞地道:“潘长旭这人走路就这么个‘调’:风风火火,急匆匆的,节奏感极强,我一听,就有谱气。”
龚老师偶露峥嵘的非凡听功,令我心头顿生一种惬意的感觉:看来,这龚老师对我是格外关注的哟!
身材墩实,常打赤脚在田间地头奔走的刘汉振老师,是一位公认的实干家,亦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诲人于不经意间的长者。当年秋收时节随刘老师在田间进行估产时发生的一幕,至今仍清晰地储存在我的记忆中:面对一望无际的层层稻浪,刘老师微笑着对我道:“小潘,我出一道小考题考考你:当大面积的稻谷成熟该收割时,你说我们该咋个收法最科学?”此问话音未落,他继而进一步提示道:“请注意,这稻谷有已熟透的与基本成熟可收割的之分。”
我不假思索地答曰:“当然是先收熟透那部份啦。”
刘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道:“回答得太快了点,好好想想再答。”
我即刻领会了刘老师的良苦用心,他这是在委婉而明白地提醒我:答题有误。在与他双眼对视的瞬间,我还捕捉到他传递给我的这样一条信息: “答题,不能只图快,得用心想明白了再答!”
用心“盘算”下来,我蓦然间发现,自己先前那种不假思索的回答的确太小儿科了点。你想,倘若你先去抢收熟透的那些,回过头来,先前八九成熟的不也熟透了吗?那抢收不就老围着熟透的疲于奔命了么?须知,那熟透的稻谷是不经碰的,熟透的面积愈大,脱落掉地里头的就愈多的呀。所以,明智的选择当是:忍痛先放下熟透的,集中优势兵力先将尚未熟透的那部份抢割了再说。当我将这经权衡利弊后的 “答案”道出后,刘老师他双眼顿时眯成两条缝,乐呵呵地道:“这就对了。人生啊,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答题的过程,无论那题是何种类型的,都得用心想明白了答。”
还记得,这刘老师于1970年10月间,提名我加盟科技组,其提名依据是:潘长旭积极肯干,好动脑子,又能写文章。这事,虽因一月多后我应征入伍而“搁浅”,但刘老师对学生的提携之情,我是难以忘怀的。
1970年12月初,当我的应征入伍事宜面临迈“坎”的关键时刻,当我这个父亲为国民党员、伪甲长,母亲被莫须有冠以“污损毛主席光辉形象”(实情为母亲将换下的旧画像工工整整置于床席下,详见《母亲与政治》一文)罪名的知青成为有争议应征知青的关键时刻。龚维敬老师、刘汉振老师、生产队指导员思绍章、公社武装部段部长等异口同声地道出此仗义之言:小潘这样的知青如不属可教育好子女(当时时局下对家庭出身欠佳知青而言),恐怕说不过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负责征兵工作的县武装部副部长王蓝辉。这王蓝辉副部长,与我非亲非故。但在对我应征入伍取与舍的抉择中,他最终仍选择了我。难能可贵呀,在那极左年代,将父母有历史或现实问题的知青接纳入伍,是要担政治风险的啊!可我,承蒙师长们的厚爱与信任,居然能以极特殊“个例”应征入伍。我,当属幸运儿。
关纯,不,应当说盈江,当是我人生转折之福地。与这福地结下的情结,乃是我这有福之人用之不竭的福气哟!
(载2013年总第23期《德宏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