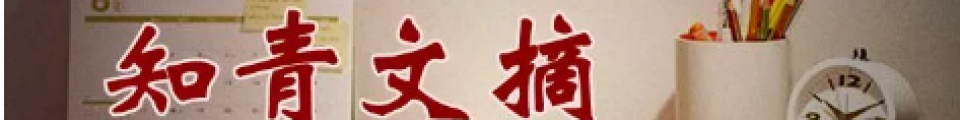那一代人有太多的“怕” “我们不愿意离别原地正如我们父母不愿离别上海的心情一样。” 我要好好想想,究竟在哪里扎根 李宁,1983年出生,2002年独自回沪。父亲是上海知青,在甘肃天水工作三十多年,目前尚未退休。母亲是浙江嘉兴人,退休后已经回到嘉兴生活 “我从来就觉得自己是个西北人,可对上海的感情特别微妙,说不清。”李宁说,他可能算是最后一批回沪的知青子女。2002年,来上海时他已经19岁,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个西北人,而上海,真不知道该称为故乡,还是异乡。 十多年里,他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上海这城市可能不太适合我,可一直有想找寻自己的一个点。” 和1990年代回沪的知青子女不同,他的怕与爱更有“现代感”—城市生活不易,但她的确有能给人生活的存在感,和更多的机遇。与此同时,李宁也担心失去自由、和他所需要的人和人之间浓烈的感情。 我回来晚的原因,是原来在甘肃省队踢球,集体户口,迁不了,下队之后才把户口迁回来的。2004年年底才把户口迁回来,也算是最后一批。 回到上海后还踢了两年球,当初是想学点东西回甘肃当教练,但那时候中国足球太黑了,就没回去,直接工作了。上海工作机会比较多,刚好我有一个机缘,进了一家报关公司,做车辆调度,港口集装箱的查验。 那时候,感觉不是很好,没有一个朋友,一切都是陌生的,同事也很少打交道,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住也住在办公室。 我爸是上海人,但他反而有点“偏西北”。去得太早了,差不多十六七岁,基本上被同化了。我对父亲的记忆太少,从小我们的沟通特别少,他爱喝酒。妈是特别想回上海,当时和我爸结婚也是因为我爸是工厂里的上海人,她就想嫁给我上海人有一天可以回上海嘛。她老跟我说,做人要有城府,要精明些,可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和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特别微妙。我生在上海,但是从来没在上海生活过;虽然在西北长大,血液里流淌的又是江浙一代的血液。有时候莫名就觉得这个城市像是自己的故乡,有时候又觉得特别陌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想在这个城市待下来,但是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一个点。 我情感比较重的一个城市是兰州。16岁,进了体校,彻底地离开家了。除了训练非常累,非常辛苦外,剩下的时光都特别美好。人很少,大家全认识,经常出去一起凑钱吃饭,去酒吧喝酒。大家都没(钱)了,找别人,骗别人的花。就这样子一直过,过了很多年。那时候西北,喝多了碰一下,一个眼神不对就要打,而我们是最团结的一批足球队,不管什么事我们都是一起上。 在兰州我接触的人特别多,这才让我会有一段想要到处走的渴望。我想念那些朋友,他们曾经有很多故事,自己开个小酒馆,经常会出去,在路上那种感觉。 因为有了那段美好,回到上海才一直在思念着兰州。当时我的网名都叫“灯火皋兰山”。 可我一个兰州朋友就说,李宁是一个西北人,但他又是个上海人,他很仗义,但他有时候又很“吝啬”,“吝啬”的意思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值得,我不太愿意去做,我可能会让对方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 我在上海遇到的挑战是跟上海人的那种性格不搭,做事方式不一样。 有时候和认识的上海本地人聊天,觉得他们跟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有的人活了20多岁没有出过上海,我就觉得好奇怪。有些人只知道上班,到月末拿工资出去吃个饭,玩一下,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的生活就是有工资拿,有好的住的地方,有一帮同学在一起,就觉得可以了。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两次出去旅游的机会,他们上车打牌,下车打牌,不出去玩。 还有上海人的优越感太强,他就觉得上海是最好的,除了上海以外,别的地方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不喜欢一个城市太大,太不方便,人的情感交流太少。我妈说过,你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可是,上海又有我很好的朋友。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他长得又不像上海人,特别粗犷特别黑,就是一个上海人中的西北人。我去上海只有找他,他随时随地的能来陪我。我们可以互相聊心事,不管对方有任何方面的困难都可以二话不说,只要有能力,全都给你搞定。 在上海的时候,总想离开,但是我又不知道选择去哪里。2010年的6月,我回兰州,本来是想去赣南,刚好夏天那边泥石流塌方车通不了,我一觉睡起来买一张票就去拉萨,一个人背着包。下火车,闻到那种空气,太纯粹了。在拉萨待了十天回到上海,我就想,这样的生活,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状态,我想为自己活一次。后来就辞职去了拉萨,用三年时间把我曾经梦想要干的事都干了。摄影记者我做了,开酒吧我开了,做客栈我做了。 我一直把我自己当作一个西北人。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上海人。她可能就是一个待过的城市,但我对她的感情好复杂,无法描述,一直在矛盾和纠结,我是留在这个城市还是离开这个城市。
作者:谢岚(本文转载自东方网 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