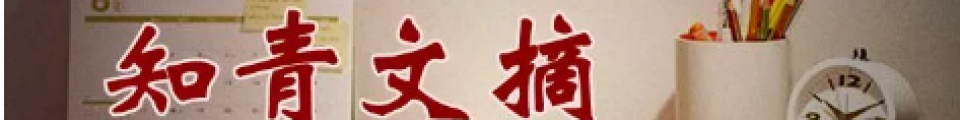原创: 顽童小逗豆 无为而无不为
2017-06-09
下一年,我们去中缅边境德昂和景颇族村寨,更深入体验了当地生活。第一次坐草车在村里转悠,坐拖拉机去一寨两国参观 ...
带队的邓老师曾在临近县当知青,熟知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某处地貌,一个生活场景,总引出一段知青故事。我们很兴奋。遥远的过去,被时光隔开了残酷与厚重,留下魔幻现实的滋味与想象。
据邓老师说,刚开始,知青一天五个工分。抗议无效后,罢工, 步行入山,两天两夜,从盈江走到瑞丽。在莽荒大山里,饿得发昏,汗湿了衣服,脱下拧干,再穿上,到畹町桥才吃上第一顿。
罢工有效。一个月后,知青一天八个工分。
实习时,我们坐着车,重温了邓老师走过的路线,看了畹町桥。听着故事,感觉他不再那么严肃,开始叫他老邓。
知青故事给田野带来了魔幻感。一天,学生回来,说村里还住着两位老知青,在村头有一栋两层楼房,村里人叫他们孙老师和李老师。传言,为纪念知青四十年,2008年他们退休后,从昆明步行回寨子,历时28天。村民很感动,给他们划了一块地基,十亩山地。
我们激动了,冲出去,试图接近他,但总被拒绝。学生说:“李老师绝对跟你说,‘下次再说!’”
我在公房遇见孙老师,很高大,留着艺术家的胡子,背个大包,精神抖擞。经学生介绍,他跟我握手,说从云南艺术学院退休不久,现在更喜欢住在山里。“我认识你们邓老师”,他跟我强调说。我很激动,想找机会跟他聊聊。
"我现在忙,下次再说" 他转身,准备离开。
"下次是什么时候?" 我追问。
他微微回身,挥手致意,"下次再说"。
走出五六米,又回头,挥手:“下次再说!”
我们目送他离去,思考“下次再说”是什么意思?
正主不理,我们跟村民刨根问底。两位老知青在村里很受尊敬。孙老师当时是军队篮球队员,技术很好,且为人老实。一次,有人打铁,铁屑飞入眼睛,他几十公里山路背着到县城医院。村里有好吃的,如抓到一条鳝鱼,都分他一半;各种活动,如祭祀,党员活动,婚丧嫁娶,都叫上他。李老师是赤脚医生,也接生,满山各寨跑, 救了不少孩子。他们的儿子在本寨出生, 被认为是景颇人。
村里一老人说:“他们离开时,房子、牛都给了我们。现在给他们分地,当是还他们。他们儿子生在寨子,是我们景颇族,是我们寨子人。”
知青故事, 开启了我们对人类学的想象, 也燃起了我们的八卦热情 —— 边境异文化,熟悉而陌生的知青,遥远而奇幻的岁月 ... 可惜,孙老师拒绝见我们。
老邓也很激动,田野中遇知青,唤起无数回忆。电话联系孙老师好几次都不通,就决定直接闯进去,一路还打着电话。到门口,两条凶猛的大黑犬对我们狂吠。十多分钟,屋里没有人声。
我们徘徊在门口。暮色渐起,雾气朦胧。当时正是雨季,风雨飘摇,山路泥泞。风声、雨声、犬吠声、声声入耳,水气、土气、心头气,丝丝环绕,我们既期待,也失落,隔着雨帘夜幕想象遥远的知青时代。
电话终于通了。李老师在昆明,她电话了孙老师,让他出门来接。“家里领导发话了,事情才好办”,老邓说。
孙老师先带我们参观房子。两层, 柱子是路灯杆。所有一切,包括每一个钉子,都是他亲手建的。我们看到他家里有七八个建筑和装修的工具箱。
“我这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还没坐定,孙老师就出了房屋,不一会,拿进一串芭蕉。“我自己种的,非常甜,想吃时就去摘,就在屋子后面。”
一坐定,孙老师说:"爱人下命令, 说要好好照顾老邓。" 本来,他从不接受采访。人来了,喝口酒,送客。缠着不放的,他就躲到山里,一连四五天,“我在山里找吃的,能活!”
“如果是张老师带来,我也会跟你们喝口酒,然后请你们回家。”他指着我说。“你们太有福气了,” 他手一挥,跟学生说,“有老邓带着来。”
我瞟了瞟门口趴着的两条大狼狗,没说话。
两位老师慢慢说起许多往事,我们也陷入了对过去的想象。当时的知青, 要么是黑五类之后, 对体制失望, 要么是工农兵后代, 积极热情, 要么介于中间, 属逍遥派。 孙老师是革命派, 相信"毛主席的红光压下黑九类"。他积极劳动,每天都是10分的满工分, 还经常加班, 一年3800工分。他枪法好, 德宏民兵队第二名, 配枪和一千发子弹。
"我们不拿扒(云南话,稀软之意)工分, 思想好, 劳动也要好。" 他强调说。
孙老师嗓门大,中气足,整个人透着他的追求和精神。他“不论多么艰难, 都不放弃,” 努力做到上知天文(头上扬,右手高举),下知地理(整个人滑出沙发,蹲下,左手指地),既要学知识,也要有体育(上跳下蹲,摆出骑单车状)。
“在需要你努力的时候,你要有能力去做,”他站起身,大声说,双手朝虚空重重拍下,离茶几半米高停住,带起一阵风。茶几上酸奶吸管的塑料包装飘起,慢慢落地。
我的目光随塑料缓缓飘落。抬头,环视一周,学生有一脸震惊,有茫然不知所措 ... 很安静,衬着孙老师的激昂。
那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孙老师说,“当党和国家需要时,就努力付出,对自己也是好的。"啪地从沙发上弹起,笔直站立,昂头,胸口高高挺起,“比如,抗美援朝时,没有武器,人可以去堵抢眼。”
老邓是个逍遥派,不关心政治,总想把话题带回生活,每次抽空问一句,孙老师大手一挥,把他推回沙发边,继续自己的话题。
老邓有执着的浪漫情怀,追问孙老师的爱情故事。当时,李老师是德宏知青标兵,远近知名,是不是看重了孙老师的憨厚, 可依靠。李老师怀孕时, 条件艰苦,孙老师只喝点水汤, 菜叶都给李老师 ...
那一秒钟,孙老师好像有点不自信,微微低头,放低声音:“这是女人最看重的男人品质。”
随即,他抬头,手一挥,又把老邓推回沙发边:“这些都是私人的事。个人家庭的就不要问了, 我们只说国家的,只说国家的。”
我们哄堂大笑。孙老师有点尴尬,转向老邓,用云南话说:“那个时候,我高一,你还是初一吧?”老邓点头。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事情他还不懂。”孙老师转向学生,用普通话说。
熟悉了孙老师的气场,学生开始问国境两边居民的生活。孙老师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和政治变化翻天覆地,但没变的是,境内外人们依旧是亲戚,国家和市场阻挡不了边民千百年的亲属和贸易关系。
而且,边境多民族混居,生活彼此联系,性格和气质却迥异。傣族善经营,有一分利都要赚, 景颇今天有酒今天醉,德昂自卑心太强, 长期处于弱势。我们所在的雷贡,是德昂的佛教圣地, 如一把大伞, 庇佑境内外大片德昂土地。
坐在学生中间,听孙老师演讲,我有点恍惚,心绪开始漂移,却更深切感受到知青一代的精神与气质,理想与热情。研究边境十多年,我慢慢熟悉当地大事小事,也开始了解区域历史,但看到历史在个体身上的鲜活展现,遭遇令人感动的不理解,听到悲怆的冷笑话,我感觉到多年未曾有过的文化冲击。
孙老师说,当时,地方居民最感谢解放军和医疗队(北京队和上海队)。人们说,医疗队是中央派来的亲人。工作队没法深入村寨,真正深入的是知青。在经受初期的文化和生活震撼后,知青给边民带来新的知识和理念, 改变着当地社会和人心。知青教汉文, 传授知识, 培养了国家下一代,奠定新一代边民的知识素质。
“知青,改变了当地社会。这里很多年轻人,都是我们教大的。”孙老师很自豪,当地人也很感谢他。
而老邓,一直都在说一辈子感谢当地人教会他触摸人生的丰富可能, 给了他人类学的启蒙,他的“山寨版人类学。”
我感慨的是,这些都是他们数十年生命经历锤炼而成的人与人的关联,人与社会的交织,及人与环境的相互改变。相较而言,感觉自己的人类学立场有点苍白无力。人类学家理解他人,并抽离出来,始终带不上生命在时光中的印记。
村里领舞的大妈早看透了这一点。大妈数次带学生走四五公里山路去乡政府参加广场舞,快半夜才回。老邓带我们跟大妈夫妇聊了一早上,说起知青时代的点点滴滴。大妈感慨说: "以前只有一个政治思想好、劳动不好的, 现在来了一大堆,每一个都是思想好,劳动不好。"
我们大笑,有点酸酸的无奈。当知青时,老邓,孙老师,李老师都积极参加劳动,队伍中只有一人靠嘴皮子活,村民看不起他,回城时给的评语最差。我们来实习,每天访谈,观察,说很多话,写很多字,想很多问题,却很少参与劳动,没有生活着当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