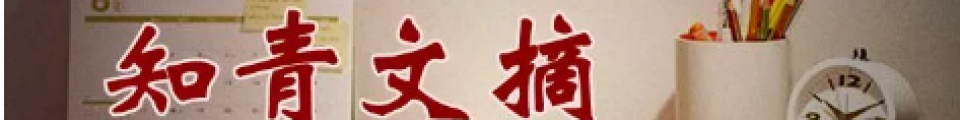1969年4月,春耕开始了。每天刚放亮,人们就到了地头干活,日落后才休息。繁忙的春耕生产,使军宣队、贫宣队都撤走了,一切都服从于播种,只有春耕顽强地支配着人们的活动。
虽然我是孤独的,但我面对无力扭转的现实却坚持己见,这样就在偏激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我这个做法叫“不服管儿”,是队干部最痛恨、最讨厌的行为,虽然我是可以谅解的知识青年,但人们仍是议论纷纷,满城风雨,对我形成了压力。
在青年点内我被孤立,在生产队里我被议论!严重的形势让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又一个难以理解的做法被我采纳了——回家,躲避风潮!
于是,我刚从沈阳回来没多久就又回去了!这次没人送我,孤身单行。在家闷了半个月。我认真思索,终于认可了形势的变化,于是起程回乡。
用愉悦的心情放眼五月的新堡,山野换新装,蛙鸣跃水绿。山川神奇地更换了景色,复苏了万物生机,我带着一路春色走进青年点。
我问吕洪财:“谁撬了我的箱子?”他立刻摇着烟袋锅说不知道。我又奇怪,你24小时不离这个屋子,怎么会不知道?但我奈何“吕大爷”不得,只好不问了。
同学们下工回来了,竟没人和我打招呼。看我一眼的同时,必看一眼那箱子,眼神中闪现出一丝异样,大家都感到某种不自在。
最终,还是我先问:“谁撬的箱子?”无人回答,空气骤然紧张,这证明了我的判断:歹徒不是外人,不是女同学,就是男同学中的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
“凭什么?你们凭什么撬箱子?”我提高音量,很有火药味地逼问,还是没人回答。沉寂让我明白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歹徒当时得到了众人的支持,现在也得到了众人的保护,撬箱子体现了众人的心愿,我是孤独的受害者!
我在夜里出现了辗转难眠的现象,仍思考着自下乡以来发生的事情,不由自主地探索“撬箱子”的原因。这件事对我打击非常大,甚至于思维紊乱,在以后的日子里又犯了系列错误……
以后的事实表明,“撬箱子”事件把我推到了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是农村生活的又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