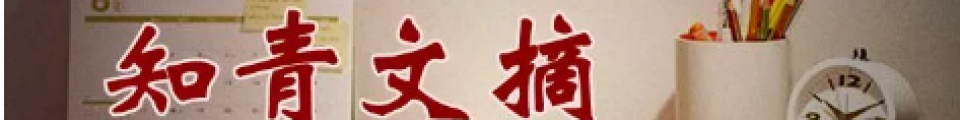总有一些事在记忆里挥之不去,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紧随着知青运动的风起云涌,我们全家也被滚滚的政治洪流裹挟着从南京下放到苏北农村。
我刚小学毕业,最小的妹妹才一年级。记得到生产队时已是掌灯时分,队长把我们带到小学校,点着煤油灯,召集了部分老乡开了个简短的欢迎会,具体说的啥已经忘记了,只记得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跑来跑去,围着我们好奇地张望,社员们问这问那,苏北话依稀听懂一点,说我们姐几个长的好看…
乡村生活就这么猝不及防的拉开了序幕,不管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愿不愿意接受它,从这天起它就是我们的全部,隔着四十多年的帷幔,每次掀开它都有疼痛,当然也有美好。

(一)过年
中国古代沿袭下来过年的习俗,最早是躲避“年”这个怪兽的伤害,后来演变为家家户户贴红对联燃放爆竹喜气洋洋守更待岁坐享美食的传统节日“过年”。
乡人的年味更浓,记得家家户户包饺子,做豆腐,蒸馒头-有玉米的小麦的还有糖三角。那个年代大家都穷,物资紧缺,但是,过年乡民们很重视,再穷也会倾力奢侈一把。生产队分了黄豆,我家也有份,在老乡的指导下也自己做了豆腐,这点石膏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在黄豆磨出豆浆后,倒进大锅煮沸,将石膏调成石膏浆冲入煮沸的豆浆里,用勺子轻轻搅匀,数分钟后豆浆凝结成豆腐花。这个过程非常神奇,我亲眼看见小学胡老师的家属(苏北管老婆叫“家属“)我们叫她胡妈妈,她点膏豆浆成豆腐,令人兴奋。
那时候,没有冰箱,冬日里挂个篮子在院子里,做冰糕豆腐,母亲会给我们做肉糜汽水,在寒冷的春节里,冻豆腐放到肉糜肉汤里,一丝丝的很有劲道有嚼头,加入大白菜、葱花,热气腾腾的一大碗喝下去,浑身暖和和的,特别满足!(小时候基本吃肉糜,省着点呀,红烧肉难得才吃)
母亲有几个拿手的川菜:珍珠肉丸子,将肉糜佐料调好,糯米浸泡好,肉圆子周身一滚,再上笼蒸上二十分钟吧,软糯喷香的珍珠丸就好了,令人垂涎欲滴;其二粉蒸肉,酱油佐料拌好一块块大肉,撒上四川老家寄来的炒米粉,也是上笼蒸熟,外粉里肉,肉嫩粉糯肥而不腻,那个香呀!其三青椒塞肉,绿红相间,色泽上就吊起了馋瘾;其四回锅肉,有肥有瘦的肉切成片,跟辣椒爆炒,母亲说炒辣椒要多放盐,把辣素锁住再和肥肉一炒油出来了,辣椒油亮亮的,肉走了油酥脆焦黄裹着辣味,那叫相得益彰,一口咬下去,唇齿生香,特别下饭。
还记得若运气好的话,生产队翻鱼塘,我们还能分到条把活鱼,这个年也算年年有鱼(余)了。
(二)哭嫁
是下放的第二年春天吧,听小学校胡妈妈说,前村那个黄家姑娘要出嫁了,在家哭呢,我们跑去看了,窗口猫着不少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姑娘,为了啥?一双解放鞋!黄姐姐十八岁了,早几年定了亲,明天是出嫁日。十八岁了,她没有穿过一双买的鞋,都是自己纳鞋底做的土布鞋。
自打懂事起就帮着爹妈带弟弟妹妹,身为女孩,读书想都别想。她想要一双解放鞋想了好多年,现在要出嫁了,又重提旧事,越想越伤心,在娘家来了个最后一哭,那哭声真的好凄厉呀,顿足捶胸,惊心动魄,一边数落着父母偏心,一边睡在地上打滚,看得我汗毛直竖。
这一幕近五十年了还难以忘怀,那撕心裂肺的嚎哭至今还响在我的耳畔!令人揪心!穷呀,挣工分的父母没啥能耐,只能厚子薄女。
那时,一个工才6分钱,强劳力一天记7分工,家里有3、4个劳力的年终分配能勉强拿回全年的口粮,最好的还能有数百元结余。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家中缺劳力,子女多且小,年终结算是透支的,还得想其他办法交清透支款,才能拿全分到的粮食。
每到春天青黄不接,就得靠政府吃借销粮。
黄姐姐家应该就是缺少劳力的贫困户。一年下来连粮食都有缺口,还要供2个弟弟读书,那有闲钱?
除了下地干农活,农民不许干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队里有的农民自己编芦席卖也是偷偷摸摸的。
这些是我大姐告诉我的,她那时是生产队记工员兼会计助理。她说去过生产队保管员家,三间漏风的草屋,5个孩子,最大的14岁,土柸上用玉米杆子扎的就算床了。自编的芦席破的没了边,一堆破棉花就是被子。估计还是当年父母结婚时的被子。
若再摊上个病灾的那就是家破人亡呀!记得队里的民兵连长部队复员军人识文断字的邵大哥,突然得了肝癌,就这么去了2次医院回来了不治了,几个月后死了,留下了遗腹子,邵大嫂欲哭无泪,有时来我家坐坐哭哭,她孩子还是我给起的名字“红慧”,希望她长大能聪慧,日子过得红火。

摄影:吉它木影
(三)造冤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非常封闭,我们在学校里读书还分男女界线呢。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生产队一位年轻姐姐突然得了妇科病,被父母族叔伯们议论,认为她作风不好,要打死她,年轻姐姐跟妈妈同姓,一直有来往,可怜罗姐姐半夜敲响我家的门求救来了。
妈妈年轻时地下党,职业又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公务员,从党性和人性(民性)来说此事管定了。就这样妈妈亲自陪那姐姐去县城医院做妇科检查,结论是“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由于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所致,完全不是愚昧无知的乡党们想的那样,医嘱:减轻压力多喝红糖水必要时服点当归黄芪等中药即可。
此事幸亏妈妈插手,那姐姐后来跪地叩谢妈妈救命之恩,为她洗刷了不白之冤!那个年代女孩子的贞操比什么都重要。此后罗姐姐如获得了新生,人也变得开朗漂亮了。
其时我读初一,没有生理课,对于性我们压根儿不懂。针对此事,母亲专门开了家庭会议,反复强调:女孩子贞操比生命都重要!
事实是自打我们长大进入学龄期,母亲就特别重视贞节教育,规定姐妹5个晚上不许单独出去,就算学校有事,必须班主任写条子有姐妹陪同。
升入高中母亲更是草木皆兵,家里只要见到男同学就反复盘问。如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母亲似乎网开一面说,三子脑子活络,自己注意就好呵呵。
(四)暗恋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只有一条路到广阔天地去。那是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问题之后,知青的待遇已经得到了改善。我去的郊区峰山林场条件不错,有集体宿舍集体食堂,但我特别节约,总觉得自己这么大了应该减轻家里负担,记得我一个月只吃了1.9元的菜金,很傻的不舍得吃荤菜。
全国学大寨,我们的林场本来是丘陵地带,盛产砀山梨,但上面指示一刀切退林还耕,引水灌溉种起了水稻,我们插秧的任务很重,记得赤脚站在水田里,那蚂蝗顺腿爬,血顺着小腿流,开始很害怕觉得恶心,慢慢习惯了,也就随它去了。
知青生活很枯躁,白天劳动晚上也没有娱乐活动,我就拼命地读书呀,很多小说都在那时候读的《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牛氓》、《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在劳动休息的间隙给知青伙伴们讲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小说那些爱情的细节,很有听众缘哦。

知青生活单调苦闷,几位南无(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老师的孩子)子弟抱团取暖,也很有才华,常常在晚饭后,在宿舍门前的小广场上打球,或自弹吉他拉着手风琴唱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们走在大路上》《打靶归来》很令人振奋。我是爱唱歌的偷偷的跟着哼,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呢。有一次听到一首陌生的歌,调子凄婉引人入胜,后来听说是被批判的《南京知青之歌》,我的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下来了…
此时此刻我们也进入了青春期,知青男女插友之间的感情暗流涌动,女知青帮男知青洗被子缝被子;男知青帮女知青干体力活很常见。
有好几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个名字中有个巧字的上海知青和某傲气的南京帅哥打得火热。有意思的是,某军人后代男知青也是我们的团支书看上了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女儿,老是找她谈心,说一帮一一对红哈哈。
爱情的故事在一对对男女青年间每天上演着,给艰辛的知青生活带来一股股清流。其时,我心里也有个暗暗喜欢的男生,我和他经常一起出黑板报,我编稿,他抄写,倒很默契。插秧的时候,他手特别快,割麦子也是他割完一垅会到对面接应我,我的心里暖暖的,但谁也没说,朦朦胧胧的很美好。
20年后我们知青有一次聚会,我才知道林场知青成了2对,一对是我们的知青男队长和女队长,姐弟恋,男生高大威猛特别会照顾人,女生小鸟依人,他们好隐蔽呀,当年总见一起谈工作,哈掩人耳目呢。另一对我们的场花后来被提前招到县广播站做了广播员,男生老县委书记的儿子官二代吧,嗯很般配。
至于我喜欢的那个知青,后来考上了北师大出国了,杳无音讯。
(五)殒命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陆续有知青病退、招工返城的消息。我大姐1977年初被招工走了在南京燕子矶化工厂,我们全家欢天喜地先送走了大姐回南京。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底,我们全家搬回了南京。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一切都在复苏,百业待兴,思想解放,人心思变。
十年,我们的青春汗水洒在了苏北这片贫瘠的土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记得我参加过一个县团代会,是以“可以被教育好子女”的身份才有机会去的,平生第一次住招待所,认识了同姓的姐姐,她叫张建华很漂亮,大大的眼睛似乎会说话,我们一见如故,她妈妈以前是资本家小姐,她天生的那种高贵和大家闺秀的气质很吸引我。 
摄影:吉它木影
团代会结束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在知青大返城时候,我突然听说她死了,因为她怀孕了,怕回城体检通不过,她听江湖医生的,吃了奎宁堕胎,失败了。这个消息让我好伤心,我好后悔没有留她所在公社的地址,不然怎么我也去送送她。本来她想回家的,却永远的留在那片土地上了。
回望四十年前的岁月,如一支歌,有时低回缱绻,有时高亢激昂;又如一条河,有时缓缓流淌,有时波涛汹涌…这是时代的馈赠,时代让我们成了“知青”,在凄风苦雨里我们苦闷过,煎熬过,彷徨过,然而,我们终于走出来了!比起那位姐姐,我们很幸运。我时常想起姐姐,笑靥如花的姐姐,今生今世怕是忘不掉她了。
“二湘空间”视频号开播了
作者简介: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敬请关注二湘的七维空间 后台回复“投稿“获取投稿信息好吃的包子是怎样诞生的#美食制作@二湘空间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