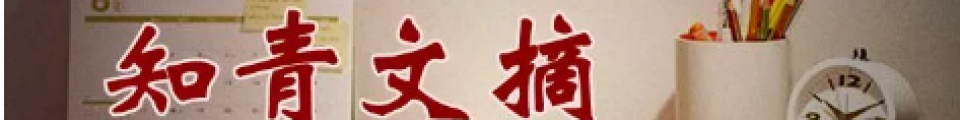刚下乡时我不知啥叫打春,趁那天挖土时队长挨着我,就问:“队长,啥叫打春?”
“打春都不懂,打春就是立春。立春就是打春。”
我还是不解,又问:“为啥要叫打春嘛,未必春天是打出来的?”
不知是他不耐烦了,还是真不知道打春的讲究,就说:“不要东问西问的,挖土多用点力。”
我不好和他理论,只在心里面叽咕‘不晓得就不晓得嘛,何必要装腔作势’,但嘴上却说:“队长,我用力挖了的。你不信看,我这一锄头挖得好深。”
我们生产队一百多号人都说立春是打春,但真正见过打春的只有肖大爷,他八十多岁,是队长的爷爷。
有天,见他在院坝里晒着太阳编筲箕,我走过去问:“肖大爷,你晓不晓得啥叫打春?”
“打春是前朝的事了,我还是在光绪年间见过的,就是鞭打春牛,我都只见过一回。这阵不兴那些了……”
他说,立春前一天,县里面要派人在东门外做条春牛,叫“迎春”;就是用竹子和谷草扎个牛的架子,再敷上泥。等到第二天,县上就派两个艺人扮成春官和春吏,在大街小巷里游走报春。
春官是官,只在前面大摇大摆的走,看见人多了就把双手往胸前一搭,做出行拱手礼的样子和众人点头示意春来了。
而春吏是春官的跟班走卒,跟在春官身后提着一面大锣,走几步就“咣、咣、咣”的敲几下,嘴里不停的喊“打春了,打春了”,招呼大家到东门外去看打春。
而此时的县大老爷则来到了东门外,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去扶着泥牛身后的铧犁,做出付认真耕作的样子,并举起鞭子往牛身上猛打三下后丢下鞭子就走。
那些围观的人马上就分成了两拨,一拨争着去抢县大老爷扔下的鞭子,另一拨就挤着去打那泥牛。
肖大爷那天到县城去卖柴火,放下担子就挤着去看热闹。他见人家去抢县大老爷丢下的鞭子,也跟着去抢。他说:“县太爷掌管一方乾坤,抢到他甩了的东西,随便都要交点好运。”
我问:“你抢到没有?”
“我运气差点,挤是挤进去了,要不是我的麻窝子草鞋遭挤脱了一只我就抢得到。”他想了一下又说,“新麻窝子草鞋哟,冬月十五才买来穿的都给我挤脱了。你说是不是差点运气嘛?”
我说:“你该去打春牛。”
“哪还有我的戏唱?等我把鞋子找到转过身去看打春牛时,人家早就把春牛打得稀巴烂了。”他像是还舍不得那双麻窝子草鞋,“可惜了我那双麻窝子,我回去找些烂布来补了好大一天,才把它补好,不然过年都该打光脚板。”
听他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打春就是立春这天举行的活动,是提示人们春天来了,要早点为春耕生产做些准备,春播春种点都耽误不起。因打春牛是在立春这天举行的,久而久之人们就把立春和打春混为一谈了。
令人不解的是,打春为啥要在东门外,西门、北门就不可以吗?于是我又问:“打春在南门外可不可以?”
“那要不得,没得规矩就不成方圆,兴起了在东门外打,就在东门外打,太阳都是从那方升起来的。”
都过了好久,生产队开会评工分,见还没多少人来,我说:“队长,肖大爷说立春那天把泥牛弄起来打叫打春。”
他说:“好的你不打听,尽去打听那些封建的东西。”
我说:“真的,是肖大爷说的。”
“蒸的,”他说,“我说还是煮的哟。”
田二嫂插嘴说:“管它是蒸的还是煮的,把那个老东西弄起来批斗,还要宣传封建思想。”
队长乜了她一眼,说:“你不要在那里来宠卵起火,我像你那样,没长脑壳吗?”
好多年后,我看到苏东坡被贬到海南时写的一首《减字木兰花 立春》,里面是这样说的:
春牛春杖 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与春工 染得桃花似肉红
春幡春胜 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 卷起杨花似雪花
我不知道打春的习俗是不是从此而来,反正知道至少在那时就有了这种习俗。
当然,我们这里受海洋气候影响要小一些,海上吹来的春风就要晚些时日,立春那天绝看不到卷起的杨花似雪花的情形。但立春这几天却能应“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谚语。只是我们这里四季常绿,少有看到有秋冬季节掉叶的树,柳树就更少,莫说沿着河走,就是沿着长江、嘉陵江走一天都不一定看得到。
对了,我记得是一九七三年在成都,正月初一逛南郊公园时,那小河两岸的垂柳都发了芽。一位游人对着随风摇摆的柳条大声念:“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另一位站在柳树下的游客用手抚摸着飘动的柳条,一字一顿的小声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里地势平坦,往小河上的石拱桥上一站就能找到登高远眺的感觉。好些游人都站在石拱桥上,双手撑着桥栏,做出付踌躇满志的样子,傲视着纤纤弱柳照相留影。
我还记得这天是二月三日,这天的太阳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游人们都像是漫无目底的闲逛着,那架势,虽说脸上不时荡漾着笑容,但更像是在苦苦寻觅着什么。
对了,我后来才想起,那些人肯定是在寻春,因为第二天就是立春,当然,说是迎春也可以。
哎,那时我真笨,真该在柳树下插块牌,上写:此处有春不用寻。
算了,不说这些,都怪自己当时没插牌,再说人家就要笑话我是:事后诸葛亮。
2016年立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