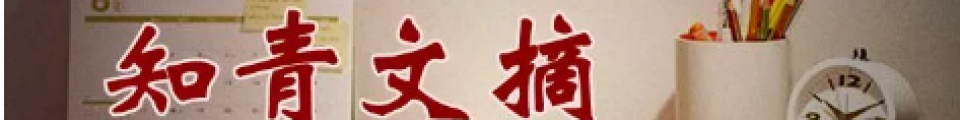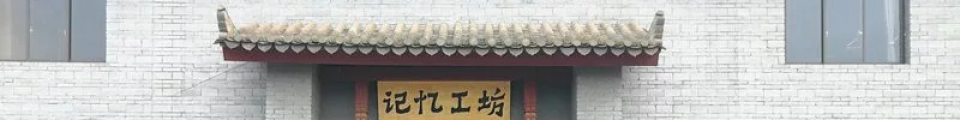组织者的笔记(上)| 余杰
余 杰
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曾经当过知青的人们在一起欢乐聚会,回忆40年前的上山下乡,纪念30年前的大返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见到了一位知青活动的热心组织者,听他讲述组织知青活动的酸甜苦辣。
怎样来告诉大家呢?他有些条件。他说,你的博客里可以讲讲这些事情,但是不要用真实的名字。有的人看了会不高兴的。再说,我也只说随便说说而已。
2、我才不与他一起吃饭呢
打电话给老黄的时候,我很吃力。一会儿说好来的,一会儿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第二次再打电话去的时候,他的老婆问我要干啥?我说,我们最近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要聚聚,问他是否参加?他老婆说,我问问他。一会儿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老黄说再考虑考虑。那我就问她,老黄在干啥,能不能来接个电话?她说,老黄在与儿子下象棋。
好,等上一天后,我再次打电话去,老黄先是问那些人来。我一一如实相告,还说这次聚会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一些在外地的朋友都专门赶来了,机会很难得啊。老黄听了以后说,算了,我不来了。为什么?他竟然说,没有意思。现在都啥时候了,聚什么呀,累不累啊。
我知道老黄的日子过得很好。回到上海以后,开始没有工作,他就倒卖服装,很快就挣了一笔钱。他就在上海七浦路上摆了一个摊,几年之后就买下了铺面。像模像样地开起了服装公司。后来,他专门做起了写字楼里“白领”们的工作服,生意很好。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当年在农场的时候我们连队的支部书记老姜。老黄是很会抓机会的,他与老姜谈成了他们单位工作服的订单。要知道老姜是一家大型国有单位,好几千人呢。一笔生意足够老黄过上一段好日子的。没想到几天以后老姜将合同取消了。什么原因呢,老姜没说。我听老黄说,我连回扣都给了这个家伙,是七浦路上另外一家公司插进来做这笔生意了。估计回扣比我多。老黄愤愤地说,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心黑的很。你别看他人模狗样的,一肚子男盗女娼。算了,我不去揭发了,说了也没用。证据呢?我只好哑巴吃黄莲啊。知青,什么知青,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你知青两个字?扯谈!别怪我,我是真的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吃饭的。
或许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老姜要来的,还要作为当年知青干部说说话。我再三劝他,过去的都过去了,不要太计较了。一切向前看。老黄在电话里狠狠地发泄了一番:“我不怪你,你为大家聚会付出了许多。可是那些当年在农场的时候就神气活现的人,都他妈的不是好人。都让他们自己去想想,那时是怎样混上去的。升官、读书、进工厂,我们在干啥?种橡胶,在卖命!他们这些人就是现在网上人家说的,知青贵族,简称‘知贵’。我才不会向这些人点头哈腰的。老子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的。”
临结束的时候,阿黄说,我肯定不会来的。但是我会叫小刘带上2000元钱来,表表我的一番心意。算我赞助这次活动。你明白了吧,以后我们小范围组织一次活动,我来做东,请请我这些在农场没有捞到一官半职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知心的朋友。
听了这番话,我无语!
(2010年7月7日)
3、我能理解他的拒绝
大戚在电话里一口回绝我:我是不会来的。
这是我们第五次聚会前我打电话通知大戚的时候,他给我的回答。怎么办,大家都在牵挂这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于是我就委托他的好朋友阿林打电话劝劝大戚来参见聚会。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大戚就是不愿意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知青的聚会,又不是一级组织,可以来个组织纪律约束。我们都是在自愿做些奉献,谁也没有要求谁的权利。松散、自愿加上一些怀旧的情结,促成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聚会。
我能够理解大戚。因为他说过,他是不会原谅那些当年在农场的时候曾经打过他的人。这些人也是知青,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而且都是在上海住在一个街道的邻居。记得那时大家一起来到云南农场,生活在一个连队里。一次,连队里的老工人家里一只老母鸡不见了。当天大戚正好请了病假在家休息。于是连队的领导怀疑是大戚干的事情。因为那时在连队里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这家少了一个鸡、明天那一家少了一只鸭。为什么怀疑大戚呢,当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食堂做饭的人反映大戚一天没有来打过饭。就凭着这些“证据”,当天晚上,连队的指导员和连长就下令将大戚关起来,严加“审问”。期间,我们的一些知青也加入了“审问”的行列,甚至对大戚拳打脚踢。那晚,大戚被打后的惨叫声在连队的院子里久久回响。大戚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偷老母鸡的事情。他强调自己一天在宿舍里休息,中午和晚上都是吃了一些从上海家里寄来的饼干。因为那天他在发烧,胃口不好,也不想吃东西。那几位参加“审问”的知青还说,你就是这样小气,藏着饼干独吞。
一夜折腾下来,大戚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大家只好将他送到宿舍里就不管他了。谁知道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那只失踪的老母鸡迎着朝阳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连队的大院里。当时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特别是那几个参与“审问”大戚的知青,个个垂头丧气,不知说什么才好。去向大戚道歉吗,大戚能原谅他们吗?不去吧,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可气的是那个指导员(也是知青)看见老母鸡回来了,居然还调侃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真的滑稽了。好了,算了。这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大家上班了。”在他的眼里,昨晚的事情似乎是无所谓的一件小事情。
大戚知道了以后,他一言不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以后就跑到场部去告状。结果是指导员向他道歉,并批准大戚立马回上海探亲。这以后,大戚再也没有回农场过。连队里也不闻不问,只当没有这个人。一直到大返城的时候,大戚自己回来了,办好了顶替的手续走了。临走的时候,几位当年曾经“审问”过他的知青想请大戚一起聚聚,赔个不是,但是大戚理都不理他们。据说,这几位在回到上海探亲的时候,在路上都被陌生人莫名其妙的揍过。有人怀疑是大戚叫人干的,但是证据呢?谁也没有。
算了,这些恩恩怨怨到何时了呢?就是这几位知青至今一直很内疚,想在聚会的时候向大戚道歉。但是人家不给你机会啊。至于那个当指导员的知青,回城后就一直没有与大家来往过!
(2010年7月9日)
4、不动的尊神
我是在电话里这样对曾经是我们在云南农场的时候当过支部书记老姜说,到了那天聚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啊。你的任务就是上台讲讲话,给大家鼓鼓劲。不管怎么说,在当年你总归是我们的领导。就是今天,你还做着领导嘛!电话的那头,沉默了许久,老姜说,话就不讲了,这要请大家原谅。因为知青的事情很敏感的,不可以乱说的。我还在位子上,这事无论如何请大家谅解。我会尽量想办法到场的。因为最近我的工作很忙,企业在改制,天天应付工人们的上访就够烦恼的。谢谢大家了。这几次聚会我都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实在是分不开身啊。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们的几次聚会都请他来,但是几乎没有一次成功。难怪有的知青朋友在抱怨,人家都是一些当年的知青干部在组织大家聚会,就是我们的老姜不干。从来没有看见他主动来召集大家聚会过一次,连我们都很没面子的。
我也能理解老姜,人家毕竟是企业的领导,工作很忙的。不想我们这些人,该退休的造就退休了,没有退休的也是在岗位上混混而已了。确实没有多大的事情。咱不能够与当领导的相比。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老姜对于知青问题的这个说法。我们是聚聚会,又没有什么敏感的问题。这有点小题大做了。你当你的领导,也不至于怕到这要的地步。看来,胆小一点的人可以混上去,我们这些信口开河的人是永远当不上领导的。
我才懒得理老姜与阿黄的那些事情。谁知道谁对谁错呢?那时在农场的时候,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事情谁说的清楚呢。老姜那时当上领导,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无论在学习上、工作上都很积极的。在那个年代里,老姜也是免不了要做些错事的。也得罪了一些知青朋友,留下一些至今还很遗憾的话题。但是,都过去多少年了。我们现在的知青聚会只是为了叙叙情谊呀。
打完电话,我与几位组织者打起赌来。我认为老姜这次肯定会来!理由是这次是我们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曾经在一起的北京、重庆、昆明的知青朋友都来了。以后这样的机会很少很少了。这样的聚会能不来?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组织者中的几位都反对我的这个看法,说我太乐观了。他们甚至说,要是老姜来参加聚会,他们三人把当天的单买了,不要“aa制”了!口气好大呀。为什么呢?他们理由是:老姜早就说过了,知青的聚会他是不会来参见的。他在私下里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聚聚,吃吃。弄不好还要闹点意见。有这些时间还不如在家陪陪老婆孩子。最令大家郁闷的是,老姜还有一个论调:聚会?能够给我的工作带来什么好处呢?
确实无法带来好处。知青的聚会只有付出。想着得到回报的人最好是不要来参加我们知青的聚会。我是这样看的。结果是我输了。老姜没有来。
(2010年7月22日)
5、千万要记得通知我啊
每次聚会后,我总能够接到阿娣的电话,她总是这句话:千万要记得通知我啊!我对她说,记得,记得,我哪次忘记你呀!
阿娣现在是一个人。丈夫在前几年去世了,儿子出国去了。如今她已经退休在家。听她自己说,每天她一早她到公园里去打打太极拳,唱唱歌。平时就在小区的老人之家活动室里打打麻将,玩玩扑克。晚上是最为寂寞的时候,只好一个人在家看看电视,直到睡意上来才结束一天的生活。所以,阿娣只要接到知青聚会的通知,会兴奋地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对着电话里的我说:谢谢你们呀,我太高兴了。
每次聚会,阿娣总是第一个到场。帮着搬搬桌椅板凳,招呼陆续到场的朋友。阿娣总是乐呵呵地在人群里到处转悠,又是拥抱,又是握手。大家说阿娣只要是知青的聚会就会显得年青几岁了。阿娣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的生活缺少的是欢乐。你说我现在还缺什么呢?缺钱?在美国的儿子寄来大把大把的钱我怎么花都花不完,我不缺钱!我还是缺少一种情感。从到云南上山下乡开始吃了那么多年的苦,一直到回到上海后,我与孩子他爸一起从摆地摊开始一路奋斗,挣下了这份家业,把儿子培养成博士,送到美国去了。好日子刚刚开始,老公没有福气就走了。想想我真想掉眼泪,一起同甘共苦了40年了,心里始终有他的影子。现在每到晚上,我就会在回忆与他一起风风雨雨日子中度过一夜又一夜。当然,我也会想起我们一起在云南农场的那些日日夜夜。记得老公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起说起那年到菜地里偷菜的事情。那天,我们俩偷偷摸摸地朝连队的菜地跑去,想割点韭菜好包包饺子。谁知刚跑到菜地边上,我们吓了一跳。隐约间好像已经有人在那里了。我们在担心是不是连长派了人等着抓我们呢。当我们想转身逃回连队的时候,是阿林发现我们了。他压低嗓门说,快点来,再不来就没有了!原来都是“自己人”啊!到了第二天,连长跑到菜地,看着光溜溜的韭菜地,气的他说了一句:以后再也不许发面粉了。你看,遭殃的是面粉,我们都乐了!
那时,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在一起时是相互在搀扶、帮助,这样的情谊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对于大家我是心存感激的。在老公的追悼会上,最为伤心的是我们这些知青朋友。哭天喊地,是在为我们苦难的命运哭嚎啊!谢谢你们,从心里感谢你们。所以,我才不管以前的那些陈芝麻烂事。大家能够活着回来,能够在今天还健康地活着,就是幸福!
你也不要客气,我们聚会我是没有能力帮上什么忙,尽是瞎帮忙,有时还忙里添乱。但是我的心是向着大家的。你们每次组织活动很不容易的,反正老公留下了许多,我就负责提供一些经费上的支持。花费的钱,剩下的都归我。一定,一定!因为和大家在一起所得到的这份情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记得,下次活动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啊!
(2010年7月24日)
6、至今怎么还这样迷信
几号聚会?
当我告诉老肖的时候,他在电话里想了半天才对我说:14日?不行,这个日子不吉利,带4字很晦气的。
怎么对老肖说呢?我们要聚会总不会像眼下一些年青人要操办婚姻大事时,选个黄道吉日吧。聚会吗,就是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一起聚聚而已。都是到了老头老太的岁数了,能够聚一次就少一次了。今天是上山下乡40周年,等到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还能够有多少人呢?
我只能够劝老肖:聚会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饭店也订好了,北京、重庆、昆明的一些知青朋友都如期出发了。再改恐怕不行了。再说,你也不要这样迷信,4,只是个数字嘛。照你的说法,到了4号、14号、24号我们就不过日子了?都这把年纪了,你怎么还这样迷信啊!再说,定这天日子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那天是你的休息天,你当交通协管员,难得有一天休息。事先我们几个仔细考虑过了。
电话的那头,老肖开始教育我了: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啊。这怎么是迷信呢?要不中国为什么有个黄历呢,什么事情都要选个吉利,图个吉利!我刚才看了,14日是“不易出门”的日子。你就是不信,我们那时上山下乡的时候,什么出门翻车、上山大树压死人、被毒蜂子叮死的,什么原因?就是没有算好日子。该出去的时候要出去,不该出门的就不要出门去。老天爷在天上看着的。反正你不信我信。
究竟来不来聚会?
算了,我不来了!
其实我的心里是很明白的。这些只是老肖的借口而已。我能够理解他不来聚会。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很艰难的,老婆下岗在家多年,自己也是在马路上当交通协管员。一家人的将近1500元的收入仅够维持在这个大城市里的最低生活水平。加上儿子在上大学,需要一大笔开支。老肖只好再去一家单位谋求一个夜间值班的岗位,天天晚上睡在门卫室里,一个月也有300元的收入。我们知青每次聚会都是“aa制”,少的50元一人,多的100元一次。你让老肖拿出这笔钱,真难!所以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总是想办法让他不出这份“份子钱”。这次聚会,没人也要出100元,我能够感到老肖的无奈和为难。这些关于日子的说法也许只是一种借口吧。
怎么办呢?日子是不会改变的,能够改变是我们与老肖!我试着再打电话去请老肖。
我告诉他,外地一些知青朋友点名要见你!你一定要来。老肖说,算了,我就不来了。再说好不容易一天的休息,家里的事情很多。老婆身体不好,洗洗补补的事情够我忙一天的。
我又说,你要是不来,以后就不要说我们不够朋友了。(我特意用一种不在意的口吻说这句话)再说,这次活动,阿娣赞助了,我们都不用花钱了。怎么你也要来谢谢人家阿娣呀。
电话那头,老肖不语,许久才说,让我再想想。
(2010年7月29日)
余杰,男,生于1952年12月25日。现居上海。
1970年4月从上海向东中学(原南洋女子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底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至疫情爆发为止。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50万字。
《城市记忆》系列热文
➤弄堂
➤有轨电车
➤小书摊
➤跳马
➤垃圾桥
➤大饼油条
➤灶头间
➤过街楼
➤剃头
➤照相
【小说】5号里的故事
第一章:上山下乡那年
4、荒人滩的闹剧
5、无事可干的我们
23、一针见血的二房东爷爷
第二章:大返城那年
第三章:动拆迁那年
117、再见,5号里
回城以后……——在车间
梦之城——临港新城开发始末
梦之桥
知青文汇
➤墓碑
➤偶遇记
我的后知青时代生活
➤理发小议
➤社会即景录
➤人在旅途
➤走在历史的凹陷处
➤当我们老了
➤致我们消失的青春
➤从社区出去,再回社区去的话题
(上) (中) (下)
➤怀念那个春天的年代 ——八十年代初期看过的话剧
(上) (中) (下)
➤我们的晚年
➤光环(小说)
➤1988·上海·肝炎世界
整个农耕民俗博物馆占地660余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1800平米,博物馆于2016年9月12日正式挂牌开馆运行,它是滇域农耕文化馆、记忆工坊、知青云南记忆馆、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筹)(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综合实训基地)三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共分三层:负一层序厅主要展示的是知青云南记忆馆;二层为滇域农耕文化馆,三层为二十世纪初法国农村生活景象老照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