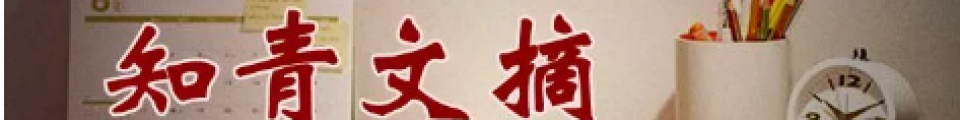十三年来,我四十万字的知青小说《梅伤》在朋友们的一路鼓励支持下,终于变成了铅字,沉甸甸的书捧在手里,心里竟然生出了几分惶恐:粗浅的认知、有限的视野、笨拙的文字,能当得起朋友们的期许和称赞吗?
《梅伤》写得异常艰难。
十三岁时,我躲在北碚图书馆的红楼里在书海中徜徉,就立下了誓言:我要当一个作家!一生之中,我数次发誓要写一本书,但都因生活动荡不安,家庭屡遭变故,一直静不下心来,因而未能兑现自己的誓言。零三年我办理退休手续时,国家政策决定把知青下乡的年限计入工龄,需要我自己到档案馆去查明我们是哪一年下乡的。我想,这也算是国家对知青极其有限的一点点补偿吧。
我拿着单位开的证明来到北碚档案局,档案局的档案室门可罗雀,只有一个年轻姑娘百无聊赖的趴在桌上打呵欠。她接过证明马马虎虎的瞄了一眼,说:“你先到财务室去交二十五元的档案查询费。”我交了钱,把收据递给她。小姑娘从那一排排快要顶到天花板的档案柜里找到档案文件,当着我的面打开,又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地查找,“找到了,你看是不是。”
我拿过来一看,文件上全是一行行用碳素笔手工填写的字迹漂亮工整的表格。
我捧着档案薄,心中百感交集,我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们生命中只有一次的青春岁月,只是变成了国家档案馆里一行行冷冰冰的数字,我们的青春、理想和爱情,我们的痛苦、迷茫和忧伤,我们的奋斗、拼搏和挣扎,我们的血迹、眼泪和汗水,通通被冷漠地强力抹去,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百年之后,历史能记录些什么?后人能知道些什么?
管理员姑娘很诧异地看着我,不明白档案资料有什么好激动的。
姑娘漠然地拿过档案薄打开复印机把这一页复印下来,又拿到办公室盖了公章,递给我,很不屑地说:“哼!听说你们知青在文革时期当红卫兵搞打砸抢,斗走资派,搞武斗,砸烂‘公检法’,把国家打得稀烂,下乡当知青又不好好出工,还偷鸡摸狗。红卫兵不好好当红卫兵,知青不好好当知青,回城了,又没文化没技术,下了岗,又哭天喊地要吃国家救济。退休了,还要国家照顾你们,给你们的知青年限算工龄,这样每月你们的退休工资可以多领几元钱了。可笑的是,有些知青还觉得很委屈,还闹着要国家赔偿,不想一想,你们下乡这些年,对农村对农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这么理直气壮的?你们有些人说国家对不起你们,亏待了你们,你们摸着良心想一想,你们又对得起国家吗!听说你们在文革的时候,像疯了似的,叫你们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你们就批斗自己的老师;叫你们炮打司令部,你们就斗走资派,批刘少奇;叫你们破四旧,你们就抄家、毁文物,挖别人的祖坟;叫你们夺权,你们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自己先就你死我活的打起来,国家都被你们打烂了。你们自己没有头脑吗?没有是非观念吗?我爷爷是南下干部,就是被当年那些红卫兵当作走资派活活打死了的!”
夏虫不可语冰。我不再和她说话,接过复印件走出了档案馆。为了这几元钱的知青工龄补偿,还要忍受年轻人的奚落,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她说的也是事实。
我们最宝贵的青春时代无谓的逝去,时过境迁,却只换来现今的年轻人不以为然的鼻子一哼,这是何等的悲凉!
文革过去了,仇恨却遗留了下来;知青回城了,悔恨仍影响着一生。这给中华民族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难以想象。
进入人生之秋,对身边的琐事都记忆模糊丢三拉四,唯独对当知青的那一段经历记忆犹新,一点一滴历历在目。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如放映电影一般,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如同昨日。我常常做一个相同的噩梦,梦到我仍然在农村当知青,肚子饿,到山上采野果子吃,梦到我考大学因政审不合格被刷下,从梦中哭醒过来……
我要写一本书!我心里对天发誓。这一生中,面对因武斗死去的红卫兵遗体,我发过誓;在知青的坟前,我发过誓;对弥留之际的父亲,我发过誓。现在,是我兑现誓言的时候了!蹉跎半生,时不我待,再不动笔,我就老之将至,空留遗恨了!
我开始认真的坐下来,静静地梳理自己的一生。谁知待文字一落在稿签上,就迅速进入忘我状态,人虽然在现实中行走,但我的意念已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从前。魂不守舍,是我的常态。以至有一次在公路上行走,竟然没有听到身后的中巴车司机急促的喇叭声,被这个新上路的司机一下撞到了地狱的门口。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外伤加内伤的我头脑却异常清醒,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死去呢?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大学还没有毕业,我也才刚退休,我的书才开了一个头。我出了车祸,哥哥嫂嫂要忙前忙后的照顾生病的老母亲,还要一天三顿给我送饭;妹妹则交警队、中巴公司的来回交涉;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没有告诉他……病危通知书能交给谁呢?我对我的主治医生说:“把病危通知书就交给我吧,我一定配合您好好治疗。我不会死的!”
多处骨折、全身瘀伤、头破血流,都是小问题,假以时日,总会康复。要命的是因猛烈撞击造成的心肌淤血而引发的心律失常,心跳每分钟一百六十多次,室上性频发早搏每分钟三十多次,而且出现了严重的急性充血性心衰,全身迅速出现水肿,连我的老母亲也认不出我……也就是说,我的小心脏随时可能罢工。只要我还活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那种痛,就是一种濒死的感觉。病房里和我相同病例的病友已死了,头天晚上还在和我说话,第二天医生查房,才发现她已经永远醒不来了。而病友的病情还没有我严重,而且还没有外伤。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祈祷,明天我一定要醒来!
上天总是眷顾那些心存善愿的人。我庆幸中巴终于停住了车,没有从我身上碾压过去;庆幸我的右手还完好,头脑也还明白,也有了绝对充裕安静的时间,有了这几样保证,在住院治疗期间,我就可以继续写作了。
我央求哥哥给我做了一块轻巧的木板,靠在床头,把木板搁在大腿上当书桌,就可以一页一页地写稿子了。
不管春夏秋冬,我焚膏继晷,奋笔疾书,进入了疯魔状态。过去的朋友一个一个的来到我面前,和我对话。写到好笑的地方,我常常忍不住自己自个儿嘿嘿笑起来。写到伤心之处,我又常常悲不自胜,泪水洇湿了稿笺,使得字迹一片模糊,只得重写。
写作的过程,就好比是把已经结痂的心灵创口重新撕开,让它血淋淋的摆在面前。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有时候忍不住伏案痛哭,写不下去;有时候感觉胸中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忍不住想大吼大叫;有时候觉得自己就要爆炸,想哭哭不出来,想吼吼不出来,喉咙哽得发痛,那种令人窒息的沉痛感,压抑得人难以呼吸。
隔着岁月的长河来审视那一段历史,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住了近一年的医院,身体也恢复得非常好,从外观上已经完全看不出我曾经历过严重的创伤。
出院后,我又进法院打赔偿官司。判赔下来,责任各占百分之五十,我倒欠十几万元。拿到判决书的第二天,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开始打工还债。
写作是深夜的事。
一年后,四十万字的初稿完成,稿笺摞起来足有一尺高。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传媒公司工作,他见我写得辛苦,遂给我买来一台电脑,并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并还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建议。从此,我的写作如虎添翼,突飞猛进。从记事以来,他只是零零碎碎地听过我讲的知青故事,觉得像听天方夜谭那样难以置信,他一直强烈支持妈妈把过去的经历写下来,说,为了我们,你们的经历也一定要写下来,不能让这段历史湮灭在尘埃中,如果我不了解我的妈妈这一辈人经历了些什么,我就不是好儿子。儿子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欣慰。
当我坐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地一边修改一边录入我的长篇知青小说《梅伤》时,我白发苍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看惯了我伏案写作的背影,只默默地给我的茶杯续上开水,为我削来一盘水果,插上牙签,静静地放在我的书桌前,然后坐在我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有时候,她就直接把苹果一片一片的喂进我的嘴里。
2005年7月24日,《重庆晚报》副刊周末版以《草根文学的庙堂梦》为题,给我作了一个半版面的专题报道。但他们不管图书的出版发行。
《梅伤》初稿,朋友常常读得泪流满面,都希望能尽快出版,好让更多的人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真相,了解那一代人的青春梦想。
那个时候,我的书稿就是我的精神寄托和生命支柱。我把厚厚一摞书稿请红岩杂志社的人指点,三个月后我去把它取了回来,上面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连指纹都没有留一个。后来,一直是连续碰壁。我已经进入晚年,早已看淡名利,悟透生死,如果在毕其一生的第一本也许是唯一的一本书里都还不敢说真话,那我应该就此搁笔以谢天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地狱的门口爬了回来,现在,每活一天,都是赚的,那又何必违背做人的操守,重新爬回思想的牢笼呢?即使有一天我会为此而死,我死而无憾,我以我血荐轩辕!
讳莫如深的历史,必定隐藏着不愿让后人知道的故事。
人类都是在对前人的质疑、否定、选择、摈弃和有限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我希望我的书在多年以后,还能够体现它的历史价值,还能够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我写这本书,只是为了立此存照,本就是写给未来的。就让它做一棵根置于民间的野草吧。
为了能够秉笔直书,我情愿再进一次炼狱。
我对书稿进行了数次增删修改,在复印店把书稿打印了十几份,装订成册,请教相关的朋友指点校对纠错。其间得到了许多知青朋友的大力支持。至今,我都还保存着朋友们用红笔修改批注的打印稿。
我的良师益友、《无声的群落》的主编邓鹏教授几年来不遗余力地从各个方面给予我巨大的提携和帮助,四处为书稿的事张罗。201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拟定出版十本知青题材的丛书,邓鹏教授推荐了我的《梅伤》,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稿被撤。邓鹏教授小到对书稿里一词一句的描述、大到要坚持做人的良知,不要改变初心的叮嘱,他都给予我非常深切的关怀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他的人格魅力时时影响着我。邓鹏教授为《梅伤》写的序言,可以说是痛切的醒世恒言;
四川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美术评论家林木教授真诚热心地帮助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使我能得到我一心想要的图画作我书的封面和插图,神通广大、朋友遍天下的林木教授亲自出面,短信电话不断,追着画家云游四方的足迹,从国内追到国外,几经周折,终于使我的梦寐以求变成了梦想成真。甚至还介绍他的画家朋友苏谦大姐为我的书画梅花插图;林木教授邻家大哥般的亲切、真诚,使我感到莫大的温暖;而且,林木教授从山东的一个会议上马不停蹄地专程飞往重庆,参加我的《梅伤》的首发式,这样的义薄云天,让我感动万分。
著作等身的著名主编岳建一大哥,给予《梅伤》极高的肯定和赞誉,字字珠玑:“没有残酷青春、深远伤口、苍凉人生、最放逐而又最集体的命运根植于作者精神血肉,何有如此彻骨的殷忧与痛切?于是,作者恪守记忆始终,甘当抢救知青历史的志愿者,历时十余年,披肝沥胆,数易其稿,砥砺成书。作者拒绝统一、规范、切割、麻木的记忆,自辟独立思索、自主精神、个性才华的不倾之地,自己向自己讨一说法,执著不懈,沉劲艰卓,担当个体记忆的骨血、灵性、天良和尊严。《梅伤》穿透遮蔽,突围禁锢,直抵当年灵肉处境,直抵个人、集体原生形态最为深隐、最为动荡、最为斑斓、最为本真而又确凿的领域,直至出经入纬、寻幽觅微不竭。该作已将文字化为生命,生命融入文字,因而篇篇章章多是血液般流动的文字,娟秀嶙峋而又富有表现力,更具体温、痛觉、声息、神韵和本真鲜活气象,遂使不是传奇胜似传奇,亦使一隅难以索解而又沉重似铁的历史真相从此不再虚无。太难为了!”
建一大哥对《梅伤》的肯定,使我在大陆出版社屡屡碰壁的沮丧得以减轻,重拾信心。我与建一大哥约定,等到机会来临之日,他要像他当年历尽艰辛编辑出版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为我编辑出版《梅伤》,让《梅伤》能够堂堂正正的摆上大陆的书店。建一大哥,我们都好好保重,等待那一天!
作家邹克纯数年前我和他神交已久,因机缘不巧未能得以相见,在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第八期杂志的发刊会上,听到主持人念优秀作品获奖名单时念到他和我的名字,我们同台领奖,才由此相见。我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为我的书写的序,给予了我深度的理解,我把克纯大哥视为知音。在文学的殿堂里能得到克纯大哥的悉心指导,我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敬意;
享誉海内外的体制外著名画家张大中先生,我觉得我和他多年前就结下了缘分。因为需要为我的书配封面和插图,我浏览了网上不下几百上千幅知青画,当我看到大中先生的《金太阳之路》等画时,震撼得连呼吸都屏住了——他画的,仿佛就是四十年前的我!相同的发辫、相同的衣服、相同的挎包、相同的布鞋、相同的景色、相同的忧伤……
更巧合的是,他的另两幅画和我书里的人物、情节高度吻合,连细节都那么相似!心里觉得这个世界真是神奇,我和他相隔数千里,素不相识,冥冥之中,我们却用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几个相同的艺术形象!分不清是我写活了大中先生画里的人物,或是大中先生画活了我书中的人物,这是天意。我和他的短信聊天中,谈到了我对《金太阳之路》的理解,他很感动,说我是最懂他的画的人,把我引为知己,又给我发来几十幅大图,让我随便挑。真正的大画家、大学者的谦虚低调,让人肃然起敬,我对大中先生的慷慨感激不尽,大中先生却说,他的画大都是被买家买去收藏,能真正欣赏到的不多。他感谢我选中了他的画,让四十几年前的人物从历史中走出来,回到了本该有她们一席之地的当下,走进普通百姓的视野,走进千家万户的书斋。同时,也使他的画随着我的小说走进了历史。
著名画家王国斌教授,他的画作《半个月亮爬上来》简直就是我书中的一个情节的场景再现!甚至我都怀疑他当时是不是也在现场!王国斌教授为了给我发清晰度高的大图,特地中断了在法国的行程,提前回国,就为了把他保存在北京家中电脑里的大图发给我。我对他慷慨同意我用他的画作《梅伤》的插图,致电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他回复我说:“周先生好,为您的坚持而感动,也为您的《梅伤》点赞!那是一个不能被忘记的时代。应该在历史上刻下其痕迹。我们用自己的作品,还原历史,解读历史,彰显出价值和意义。王国斌2016冬日”。
老知青女画家苏谦大姐,为了我的书更加完善,得知我的书里一幅重要的梅花插图还未落实,她提前结束采风,专程回重庆,利用“五一”长假,按照我的要求为我画了梅花图,而且画了几幅供我选择,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因为情节需要,梅花图还不能署上她的大名,我心里充满了对苏谦大姐的敬意和歉意,我何德何能,能得到苏谦大姐这样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苏谦大姐还把我选中的两幅最美的梅花图送給了我!说梅花图是为我画的,由我收藏最合适。我超级喜爱谦姐的梅花图,把梅花图作了我的冰雪红梅公众号的封面。
还有谦和内敛的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影视剧作家、导演王茂久会长,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扶持知青作家,爱才惜才,还为《梅伤》写了后记,给了我积极的肯定。为了给知青书籍造势,文研会专门为知青作家印制了漂亮的海报,
还举办了有数百各界人士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知青书籍首发式,使我们的书很快就获得了较大的知名度。王会长的高风亮节,虚怀若谷,让人敬佩。
还有知青朋友王泽亚,多年来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在我遇到麻烦或困难时,他总是适时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排忧解难。他在自己都不宽裕的情况下,也坚持要给我资金上的支持,令我感动不已。而且不接受我的任何回报,他说,能为朋友出一份绵薄之力,是应该的,如果说帮助我是为了索取更大的回报,那么朋友之间的友谊就不那么纯粹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友情不是在他有一座金山时赏你一罐金币,而是在他只有最后一片面包时也愿意和你分享;
还有知青朋友李渝沙,他做事细心,且有语文功底,也是我选中的十五位校稿人之一。他还主动在资金上给了我一定的资助,我把他列为《梅伤》的校对。《梅伤》出版后,他又向他的朋友推荐了二十本,为了表达对他的感谢,我送了二十本《梅伤》给他。
还有我因文章结缘的知青朋友杨中平,他心地善良真诚热情,乐于助人,当他得知我的书正在筹备出版,主动的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和较大的资助,且心底无私,不求回报,他的品格让人感动不已。
还有书法家彭天祚大哥,为了给我的书题写书名,虽然是卓有建树的书法家,但他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仅仅“梅伤”两个字,他反复在家写了两天,一共一百多幅,纸都用了厚厚一摞,然后从其中选了十幅,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彰显了一个艺术家的风范。我从这十幅中选了两幅各取一字,书名《梅伤》,是迄今为止我所得到的写得最好的字,笔法柔中带刚,圆润饱满,从“梅伤”二字上,我既感受到了梅的坚强,也闻到了梅的芬芳。彭大哥,谢了!
我的初中同学王丹娜,是我无话不谈的挚友,几十年来,哪怕我们多年不见,但只要一见面,那种互相引为知己的友情马上就可以无缝连接,岁月的激浪冲刷不了我们友情的基石。一次旅游,在贵州美丽的赤水河畔,她向我唱起了四十三年前我二十岁时创作的一首歌《小英之歌》,她唱头几句时,我完全没有反应,我把这首在当时红火了一阵子的歌忘得一干二净了。唱到一半,我觉得这首歌似乎在我生命的某个时期出现过,她望着我,继续唱,我竟然慢慢地跟着她哼了起来,那真是从灵魂里流出来的歌啊。回到家,《小英之歌》的旋律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涌现,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我全都记起来了,甚至还记起来我当时创作这首歌的前前后后的细节,记起来我是怎样一句一句的教她唱的情景。四十三年了,我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她却还记得,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分!后来,我把这个情节补写在我的书里。
还有我许许多多的知青朋友们,他们为我摇旗呐喊、加油助威,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从他们的支持鼓励中获取了写作的动力;
还有我的父母,他们生我养我,为我付出一切,为我忍受一切,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无论我做了什么,无论我遇到什么,他们都坚定不移的支持我。父母这一生所经历的磨难,父亲临终的祈盼,都是使我能直面人生,直面苦难,坚持写作的原动力。虽然他们都已谢世,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虽然他们都是平凡百姓,但在我心中,永远矗立着他们的丰碑!
还有一个匿名赞助人,赞助了我最大的一笔资金,使我自费出版的书才得以顺利进行,并要求不要提他的名字。我尊重您的意愿,记着您的情分,这一次资助,我接受了!谢谢!
《梅伤》出版后,有几个朋友分别为我举办了个人的签名售书会,一次就售出四五十本书,这样的义举,真是让人没齿难忘。
还有许多全国各地的读者朋友们,出于对《梅伤》的喜爱,还把《梅伤》买去当着礼物送给他的朋友,说这是最时髦最体面最有意义的礼物。正是因为你们对《梅伤》的喜爱和肯定,使我对文学对人性不那么悲观。
还应该感谢谁呢?
哦,我还应该感谢我自己。终其一生,我坚持做人的操守,困难面前,我没有放弃;死亡面前,我没有恐惧;歧视面前,我没有自卑;打压面前,我没有低头;贫穷面前,我维护自尊……
我感谢对我绽开的每一个微笑,感谢对我伸出的每一次援手。
常怀感恩之心,生活就不会亏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