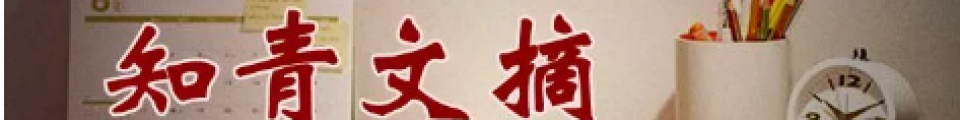详细内容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浸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啼知了,遍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敌人围剿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不下雨不走,天不黑不走,山不高不走”,这著名的“三不走”恰恰是缅共人民军在这个角落里的生存之道。一个走字,高度浓缩了缅甸丛林游击战的精髓。
缅共人民军出其不意地在雷门山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折断了围剿之敌一支精锐枪头,又迅即消失在深山密林中,与纷纷扑来的数路敌军继续苦苦周旋。
人类感官轰然恢复。此时能辨出树影和人的四肢五官,以此断定这是白天。通常是凭饥肠碌碌的程度来判定晨昏的,可是此时最要紧的并不是饿。
我捡三块石头坐灶,克锅,加水,先把我腰间十几重的米袋放空,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天的路程我将因负重的减轻面走得轻松些,我不可能先把别人的米袋倒空而自己的却老憨粗相背着,这点小算盘我也得扒扒才行,任重道远呀!
如果背行军锅的人掉了队,我就会砍些竹子来把米和水放进去烧竹筒饭,用芭蕉叶把菜包起来放在炭火中烤熟。
更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识别和食用满山遍野的各种奇花异草。
“干饭喽!”我已经能说一口地道的果敢话,一声饭令,满地横七竖八的“僵尸”马上就从梦里阳间重返人世阴间,一骨碌翻爬起糊满锅边,争用芭蕉叶、树叶、塑料布抓一堆米饭开干,进入状态之迅猛令人乍舌。
连夜行军,来不及去弄什么野菜,每个人包里都有一包小米辣,沾点盐巴咬一口就饭吃,有人顺手就从脚边草丛揪一把叫不出名来的草,沾点盐往嘴里送。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基本生活。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