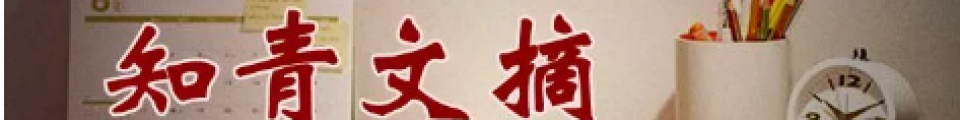怀揣轻骑队的集体照,伞哥找到了乐东县保显农场(三师十五团前身)在广州的代表老易,老易在看了那张20多个帅哥靓妹的照片后眼睛一亮,立即就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很快代表农场领导同意接收我们。
来不及看清楚海口的模样,我们在秀英码头上了农场派来的解放牌卡车,直奔乐东县。
当我们终于到达那个半坡上排列着数幢新茅屋的六连时,已经是1月19日的傍晚了。
事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贯彻实施,省革委会认为不能坐视不理,很快发函给兵团政治部,希望兵团对接收的湖南知青予以放行,发回原籍,统一分配到省内的下乡地点。
分批逃跑的计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实施的,前两批已经回到长沙,现在就看我们了。只要回到长沙,一切就好办,因为兵团没有任何理由将我们视为“逃兵”并捉拿归案。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下工回到草屋里,在煤油灯下挥笔疾书,给五班全体战友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
从连队到县城,一条大路,20多公里。从来没有一次走过这么远的距离,更遑论夜里,只有两个青春无敌、秀色可餐的女孩儿。但回家的念头鼓舞着我们,一切都不在话下。
我和端阳各自斜背着一个当时流行的绿色帆布挎包,轻装上阵。为壮胆,我们挽着手,开始“夜行军”。
开始我们劲头很足,渐渐地白天劳动后的疲劳袭来,步子不觉放缓,肚子也开始咕咕叫唤,神经的高度紧张倒让我们忘记了困倦,就是机械地走啊走,盼望县城在曙光来临时出现。
就这么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头。直到东方发白,我们才终于看见了那个小得可怜的乐东县城,我的心又紧缩了起来,似乎稀疏的路人随时都可能识破我们的逃跑企图,像母鸡拎小鸡一般把我们押送回团。
虽说好几个月没有到县城了,我俩完全没有心思去逛那条唯一的、破旧的街道。幸亏一进县城就先到汽车站,免了穿街而过的麻烦,我们径直走进简陋的候车室,一眼看到郝宝和狗伢子,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差点儿跳起来。
郝宝一改往日的笑容,皱了皱眉,意思是“非常时期,不可造次”,这让我马上想起了电影里见过的地下党接头的画面,即刻安静下来。接过车票,我和端阳去买了几个馒头花卷当早餐,大家分别上车。
在车上数端阳的话少,常常是羞涩一笑。她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物以稀为贵”,父母看得很重,回去总归有饭吃。
离候船室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我们的步子也越发急切。乌拉,回家啰!
一分钟之内,我们从满怀喜悦到希望破灭,别提有多沮丧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原来商量好的对策:万一被抓,一定要去海口的兵团司令部讨说法,因为湖南革委会的公文在那里。
垂头丧气,一路无语。这次没有跑脱也就罢了。只怕影响全团上百号湖南知青回家计划的实施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解放军那么快就判定我们是逃跑,且追逃如此迅速呢?
回到团部已经月儿高悬。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团招待所,安排男女各一间房,说今晚先休息,明天办学习班。
我和端阳坐在各自的床上,默默对视。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觉得既然没有错,团里能把我们怎么样!
百密一疏。我们想到了如果被抓,就要求去兵团司令部;却没有想到司令部把权下放到团,且要“各个击破”,现在我们只能“独立作战”了。
我很坚定地说,没有人组织,我就是想家,我爸爸去世了,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又小,我回去再下乡至少可以离家近一些,方便照顾他们。
“我们是同学,见了面什么都说,刚好我们都想回去,又听说湖南革委会对我们自己跑到海南岛很不满意,叫我们回去重新分配,所以就商量一起走。”
“我们想说,怕你们不同意。以前很多同学提过,你们都不批准。我们只好偷偷走,想着回去了再报告。”
兜兜转转谈了半天,领导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叫我回招待所好好反省自己。我答应了,反正方式是错的,我认!
到房间关上门,和端阳对“口供”,惊人的一致。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端阳也笑,抿着嘴,眯了眼,自是斯文很多。
我们逃跑被抓的事情很快在团里传开了,我姐和几个湖南知青悄悄地跑到招待所看望我们,以示慰问。进不了房间,他们就隔着有木条的窗户说几句安慰的话:“冒得事,莫着急。”
这时我才从他们口里得知,团里那么快追逃,都是我临走前写的那封长信惹的祸……
于是先按兵不动。又过了两小时,连长沉不住气了,吩咐再仔细检查。
这下糟了!端阳那里是什么破绽都没有的,我那儿呢,只把箱子上一堆杂物挪开,那封厚厚的信就赫然出现了!
两名湖南女知青在逃的消息立即上报,团部知道后命令各连队严查人数,这下又查出另两位男知青失踪。五分钟后,一辆卡车向海口方向疾驶而去。
信写好了,我左思右想,觉得放在箱子上的杂物下比较保险,估计有人找到信再跑去海口,我们至少也在大海上了。万万没料到事情就砸在这封信上……
办班3天,团领导把我们都放回了连队,表示只要我们像过去那样好好工作,就既往不咎。但原先承诺过的研究湖南知青返乡一事,却从此没了下文。
我还是当我的班长,天天早出晚归垦荒挖穴。或许是我太年轻少不更事,或许是我与生俱来的乐观让我依旧对未来怀着希望,我的心底总隐隐约约闪烁着光亮,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一个月后,团部下命令把我调到新组建的团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团宣”),任务是排练一台节目,两个月后参加师部会演,从中选拔人员组建师部宣传队。
我是带着几分感动去报到的。我刚因逃跑未遂以“戴罪之身”回到连队,没撤掉班长职务已属意外,哪会想到让我去团宣呢?何况我还顶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桂冠”!
每每从冥思中清醒,我都底气不足地告诫自己丢掉幻想,面对现实,刻苦改造,争取光明前途,然后半是惆怅半是激情地去劳动去学习,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海南岛带几丝清风的早晨……
顾不上想得更多,我高高兴兴去了团宣。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没有再回连队。
真正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世人瞩目的1976年金秋。1978年,我通过招工调到广州。1984年考进广东电视台成为记者编辑。转眼30年,如今我已经是退休的资深电视人、一级作家。还在写作,还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