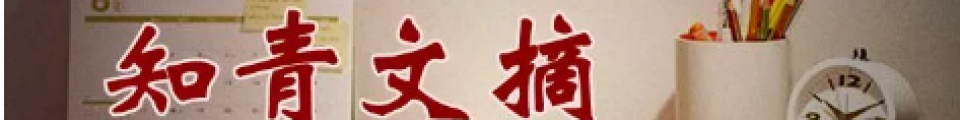猪屋生涯 消逝的哭声 不该降生的生命 婚礼上的痛哭
25年了。春去冬来,天上多少阴晴圆缺,地上多少悲欢离合,但插队的艰辛岁月,留在记忆里永难褪色。只是每当回忆起来,心底涌出的总是阵阵酸涩。
下乡5年的岁月中,我们曾在猪屋住过1年。
我们落户在江汉平原的公安县荆江区茅台公社先锋一队。这一带属荆江分洪区,沿虎渡河两岸的大堤上,有不少国家出资修建的红砖红瓦的平房。这些红瓦房在农民破旧的土砖茅草屋中,鹤立鸡群,分外显眼,这是准备一旦分洪,给分洪区难民住的,农民称之为“蓄洪房”。我们插队后,就住在红瓦房里。
住了一年多,生产队实然通知我们搬到堤脚下的一间猪屋去住,这令我们又惊讶又生气。
这间猪屋有一个辉煌的名字,叫做“百头猪栏”。根据“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的必然逻辑,生产队准备在这里喂一百头猪。这间猪屋将产出大量猪粪,将粪施到田里,毋庸置疑,粮食大大丰收指日可待了。但可笑的是,决策人只梦到了辉煌的前景,没想到最为现实的问题:哪有买猪仔的钱?即使买来猪仔,又哪去找钱买饲料?猪屋盖起之日,也就是美梦结束之时。
按说农民应当是最务实的,与土地相依为命,最清楚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底细。但是那个年代,都有点癫狂,尤其是那位政治队长,好大喜功,为博得上面的表扬,穷折腾,盖起了全大队最大的猪屋。
这间猪屋长约40米,宽约7米,一条1.5米宽的走道贯穿其中,方便饲养员给两边猪栏的猪喂食。猪栏每3米隔一间,可喂两三头大肥猪。我们搬进来后,一人一间,放一张床,搁一口箱子,砌一口灶,猪巢人占,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新生活。
住进去才发现,猪屋毕竟不是人屋,这一长溜猪屋,坐落在大堤脚下,周围水田环绕,杂草丛生。虽是春暖花开、犁耙水响之时,可以饱赏农家春耕的美景,但蚊灾令人不堪其苦。一到黄昏,蚊虫就在头上聚集,嗡声如雷;人走到哪它们跟到哪,如影随形,两手一拍,满手黑糊糊的。晚上烧火做饭,一边操持锅碗瓢盆,一边不停地跳跃,拍击。到了夏天,收工回来,一身臭汗,格外招蚊子,一边打,它们一边叮上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只好赶快洗澡,以降低对蚊子的诱惑力。
夏夜在门前乘凉也不是件乐事,虽然身上干净了,但蚊子仍纠缠不休。坐着聊天,手里的大蒲扇得不停地拍打驱赶蚊子,只要手一停,不要一会儿,身上马上就会叮个红疙瘩,有时实在受不了,只好 逃回猪屋,躲进蚊帐,每人在自己的猪栏里,进行远距离聊天。
躲进蚊帐,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有一回,我发现帐子与土墙之间有东西蠕动,疑惑间我拿起一本书打了一下,只听见“哗啦啦”一阵响,一条酒杯粗的土黄色大蛇迅速窜上屋檐,我的眼睛都吓直了,忙拿起一把锄头,但蛇早钻进厚厚的茅草屋顶,无影无踪了。那天晚上我紧绷神经,稍有声响就迅速拿起床头准备的烧火棍。还好,一夜无事,以后再也没发现此类恶物。后来有位插兄说,要是条白蛇就好了,还可以娶来做娘娘。傻笑之余,心里还是充满了恐惧。
住在猪屋,最伤脑筋的是老鼠的骚扰。这间猪屋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上,十分引鼠注目,它们呼朋引伴,不请自来,只要你稍有疏忽,饭菜没收拾好,一觉醒来或收工回来,准会吃掉一些,打乱你一天的伙食安排。一到晚上,猪屋就成了它们的天下,一个个吱吱呀呀,上蹿下跳,目中无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听之任之。有时实在响动太大,忍无可忍,我们就猛拍床板,大声呵斥几声,以求得一时的耳根清净,以便入睡。因为是猪屋,四通八达,老鼠们进可偷,退可溜,根本不怕我们围捕,有时大白天发现一个,追来追去,它居然窜进猪屋旁的水稻田,让你徒呼奈何。
这种恼人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喂了一条狗才好转。狗名虎子(知青的狗大都叫此名)。虎子来后,逢鼠必追,十分卖力,有时会勇敢地追下水田。尽管虎子主观愿望很好,愿为主人分忧,表现也颇令人赞许,但很少看到它抓住老鼠,看来还是隔行如隔山,它抓老鼠还欠火候。不过我们的日子安静多了却是事实,这说明虎子的威慑作用还是存在的,狗拿耗子的积极意义不能低估。20多年过去了,虎子气喘吁吁奋勇追捕老鼠的感人形象至今还常在我眼前浮现。多么可爱的患难小友呵!
被赶到猪屋后,我们不断向上反映,但无济于事,原来我们住蓄洪房,生产队必须每年向国家上交100元左右的房租,这对一个穷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我们知青每人一千多元的住房费、安家费,早被有关人员“开支”了。于是队里的会计(此人非常精明)就提议把无猪喂的猪屋给我们住,以节约开支,至于是否适合人居住,那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经济利益驱动人们的社会行为,哪怕是在“最革命”的年代,照样显示出不可抗拒的规律性。
住了约一年,形势骤变。1973年,中央下发了有关知青问题的文件,包括李庆霖的那封信和毛泽东的回信,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回了蓄洪房,半年之后,又搬进了明三暗五的新砖瓦房。生产队恼火透了:房子还是盖了,钱还是花了,另外还付了两年的租金,还被上面当作不关心知青生活的典型。用他们自己的话是:“割了鸡巴敬神,人又吃了亏,神也得罪了。”
下乡那天,生产队长拖着板车到公社接我们,我们沿着虎渡河大堤向生产队走去。路过一座村庄,队长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这个队有个女知青死了。我们一惊,纷纷问死因,他淡淡地说,淹死的。
几年后,碰到一位与那位女知青同队的农民,我向他打听女知青的详细死因,他说不清楚,也许是不小心失足落水,也许是自杀。于是,我听到了一段令人悲伤的故事。
1970年底,一次招工浪潮席卷了全公社,这个大队的知青走得只剩她一人。这种结局,对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来说,不啻天塌地陷。她一人留下,无异于向周围的一切人宣告,要么她父母是人民的敌人,要么她本身有问题。总之,她属于应当永远留在农村的再教育对象。
招工前,知青们共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谁也不比谁优越高贵。可能会有些知青,故意向农民透露谁的爸爸是右派分子,谁的爷爷是资本家,以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但毕竟这类人不多,影响不大。但大招工后,突然只剩下一个人,什么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可以想象,耻辱、孤独、绝望,无时无刻不在扯着这个姑娘的心。每天晚上,小茅屋里都传出她压抑的哭声,令人揪心,令人悲伤,令人担忧。于是生产队长决定将她迁到一位五保户老太太家,一方面可以照顾她的生活,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意外。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老太太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到队长家,告诉队长女知青出去洗衣服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队长一听急了,马上通知全队的人分两拨,一批沿虎渡河寻找,一批在田野上寻找。那个晚上,人喊犬吠,全队人都没睡好觉。
最后,在人们常去的一口池塘边,人们发现了一盆拧干的衣服,一根捣衣的棒槌。一看到这些物件,嘴快的人就说,完了。几个小伙子马上下水捞摸,不出人们意料,这位女知青就静静地躺在水底。没有挣扎的痕迹,没有恐惧的神色,脸色很平静,如同在恬静的梦乡里,如同在她日夜思念的母亲怀中。
一对老三届的知青,结婚了。
他俩没法不结婚。所有的知青,除了他俩,都走了,都回武汉了。招工的工作人员一看到他俩的档案,就放在一边,再也不会多看一眼。他俩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他俩生在红旗下,长在困难时期,“文革”中失学,然后被上山下乡的狂潮裹挟到农村。他俩与同代人的生活轨迹没什么不同,但他们回不了武汉。因为他俩的父母,也可能是祖父母,也可能是曾祖父母,总之,他们的上辈人中有人做过当时政治上认为是罪恶的事,现在,他俩必须承担起这笔罪孽,必须为他俩的上辈人赎罪,捐门槛。于是,他俩就与家乡武汉无缘,就必须继续无限期地在遥远的乡村务农,无限期地接受再教育,于是,他俩想到了结婚。
既然要你扎根农村,就必须以某种生存方式与之相适应,结婚,则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两人一起过日子,男人挑水,挑柴,分谷打米,种自留地;女人烧火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样的日子比“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日子要方便得多。里外兼顾,日子太难熬了。更重要的是,两人在一起,可以相互安慰那颗孤独的心,那颗因对前途绝望而破损的心,至于有无爱情,那就很难说了。
一年后,结婚的下一个必然程序,生孩子,按部就班地来了。两人并不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是满怀喜悦地迎来了孩子的诞生,无论身处任何处境,新生命的降临总是令人喜悦的,何况是自己的亲骨肉。他俩幸福地当上了父亲和母亲。
但幸福是要代价换取的。“一个孩子三亩地”,这一下多了许多事,孩子要吃要喝要拉要撒,一条要求未满足,他就毫不犹豫地大哭大嚎,这也无可非议,这是他的本能、他的权利,这就苦了年轻的父母,繁重的农活与琐碎的家务中,又增添了更加令人操劳的事,他俩每天都忙得精疲力竭。
产假满了,母亲必须每天出工了,孩子谁来管?经过商量,终于有位五保户老太太愿意带,当然,要有一定的报酬。于是他们出工时把孩子送到老太太家,收工时接回来,日子比以前轻松些了。
如果就这样过下去,结局应该是很美满的,因为两年后,这对知青被招工了。只是回城时,他俩是空手回去的,那个孩子,永远留在公安县的土地上了。
后来老太太没带孩子了,什么原因,队里农民说不知道,我也没打听清楚,反正是没带了。孩子的父母就每天出工前喂饱孩子,然后下地,中途休息和收工时,就赶回来照顾孩子。几个月过去了,倒也顺利。可是有一天,当母亲收工回家时,发现孩子被被子蒙得严严实实,赶快掀开小被子,孩子的小脸憋得紫紫的,老早停止呼吸了。估计是孩子睡醒后,不停地动,被子松了,然后慢慢蒙住了孩子的脸、头,孩子越挣扎,被子蒙得越严实,就这样……
在母亲肝肠寸断的号啕声中,队里的农民唏嘘叹息,可惜哒,是个男伢儿。
或许,这孩子就是他们父母捐出的门槛?
我们大队有位老三届的知青,姓张,迟迟回不了城。论表现,他天天出工,农活十分内行。农民对知青的评价很简单也很实在,就看你是否卖力地干活。张知青很卖力,于是从小队到公社赢得一片赞扬声。
但是,每次招工招生,他就是走不了,这使生产队长一直到公社书记都很恼火,认为这不利于他们做工作。但招工招生的工作人员自有他们的标准,并且这些标准涉及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原则,农村干部们又不便多说了。
他下乡3年我们才下去,我们又陪他一起干了5年,这就是知青们常说的8年抗战。他为什么走不了的原因我至今也不清楚,只记得他逢人就解释:“我爸爸是红军团长,长征掉了队,但绝对没有叛党,这一点朱德的警卫员开过证明。” 这段话我们耳熟能详,每当他开口向别人陈述时,我们都知道后面他将要说的话。或许都认为他回城无望了,又加上他确实勤快,会干农活,有一家农民要他和他妹妹住进自己家。搬进农民家后,他与这家农民的一个女儿恋爱了,但有的知青说是恋爱后这家农民才邀他兄妹俩去住的。不管怎样,反正他的小日子比我们这些知青滋润多了。最起码,他回家就有饭吃,这是广大知青做梦都想不到的。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大招工的风暴横扫公安县,只要能喘气的知青都回了城。张知青也被招到沙市码头搬运站当了一名搬运工,成天赶着骡子拖运各类物资。这时他发现他与农村女友继续保持恋爱关系已不合适了,于是他提出结束这种关系,但是,农民不答应。这家农民不是一般的农民,他们家中有儿女在外面工作,据说有一位还是区干部。他们全家直奔沙市,找到单位领导,痛说张知青的插队史,并指出,若不是等张知青,那位女孩子哪会24岁了还不结婚。确实,农村女孩子的24岁,是很可怕的年龄,单位领导听后既感动又生气,明确表态,张知青若断绝恋爱关系,就将他退回生产队。
结婚是在那位农民家。男方宾客只有3位,妹妹及其男朋友,还有一位是正在华师大读书的插兄,这位仁兄特地从武汉赶回公安县参加老友的婚礼,十分义气。
婚礼上,新郎喝多了点,他端着酒杯,当着女方家人和各位来宾,拉着插兄的手失声痛哭:“亚鹏,悔不当初呀!悔不当初呀!”
前几年我回生产队去玩,好友告诉我,张知青为了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调回公安县城了,当码头调度。好友羡慕地说:“他想给哪个泊位就给哪个,人家都求他,送礼都送不赢!”
看来他的小日子更滋润了,只是我默默地想:“那是他自愿选择的生活吗?”
谢维强:男,1971年毕业于武汉市洪山区板桥中学,同年2月赴湖北省公安县茅台公社先锋一队(现公安县夹竹园镇先锋三队)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