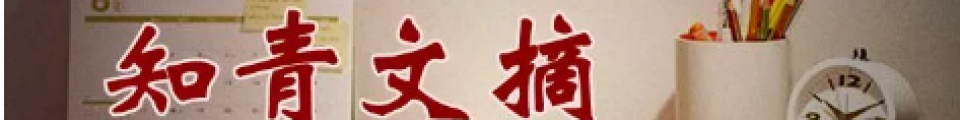何华忠,昆明第十六中学学生。兰娜,女,昆明第十六中学学生。兰娜是在何华忠被抬到总部医院时才得知这个消息的。 他说他要去,她说我也跟你去。“要死死一块。” 他们都这样说。 兰娜是这个时刻才赶来的。她哭,她扑在他的身上,捧住他的头放声大哭。她拼命地摇晃他,喊他的名字。几十个同一场战斗中负伤的战士都从帐棚里拄着枪、拄着棍,爬着、搀着出来了,他们围着她,没有一个人不流泪。 “你……不要哭了。”医生说。“让她哭!让她哭!”一个被炮弹炸去脚踝,躺在床台上的伤员狂喊着,他挥着拳头狠狠砸着氧气钢瓶。 她不哭了。她接过女护士的托盘,蘸着淡盐水替他抠洗耳朵里的积血:“我是兰娜!华忠,你醒来看我一眼!我是兰娜….”他似乎听见了,他的眼睫毛微微抖动了一下。 “他活着!他还活着!”她大叫,她对着每一个人喊,对着垂手呆立着的战地医生吼道,“立刻送他到后方,送他去抢救!你听见没有?” 人们都在沉默,伤兵们背过脸去,用肿胀的,脱落了指甲、满是血污的手指从眼角里抠着泪。 从战地的总部救护所到勐古,有两天路程,其间要穿过高山密林,要越过游击区和封锁线。而这位仅存一丝游息的战士可能在最初的一分钟里死去。 …...担架在黄昏时启程,抬担架的有两个人是临时招募来的缅族边民,其余,些人是克钦族医护,一人是救护所卫兵。兰娜紧紧抓着担架,在左右奔跑。 深夜,担架停住了。“为什么不走了?”兰娜在黑暗里寻找着抬担架人的面孔。有三两粒燃着的烟头,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她摸索着挎包里的手电筒。 接着,一个黑影一瘸一跛地荡过来,似乎是两个缅族边民中的一个,他撩开濒死者身上的军毯,用一双粗硬的大手在他脸上试着鼻息。 “不准动他!”兰娜举起手榴弹,它的拉环套在小指上,“他没有死,谁扔下他,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烈日,灰尘在脚下蓬蓬地炸着,像灰色的火焰。四个抬担架人倒靠在树荫下,合着从沟里舀来的浊水,慢慢地吞咽着干粮,木然地看着这边的情景。 她呜咽着,哀求着:“你们快走开,快走开吧!求求了,求求了……他要死了……” 四个人都走了,夜的死闸钝钝地开启,又不知在哪里闭合,脚步声忽地就消失。 翌日正午12时,兰娜护送何华忠到达勐古,108野战医院救护组对伤员进行了抢救和即时处理:M-1小卡子弹嵌在脑颅壁下,勐古及遮放都没有设备及能力施行开颅手术。伤员仍在重度昏迷之中。 当天下午4时,他被火速送往两千里之外的中国某地专科医院。7个月之后,何华忠伤愈出院。 那时农垦职工都往内地疏散。整个十六团一营的知青就剩下5个人。5个小伙子全都入伍参了战。入伍前自然是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忙活。栾新荣上前线之前最得意的一件忙活是独自一人结了婚。 最后还是纳副部长帮了他的忙为他解释说,人家是参战人员,领个结婚证也不算开什么后门,这样人家打仗的时候提着脑袋冲锋才会丢心落肠奋勇杀敌建立功勋!
详细内容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