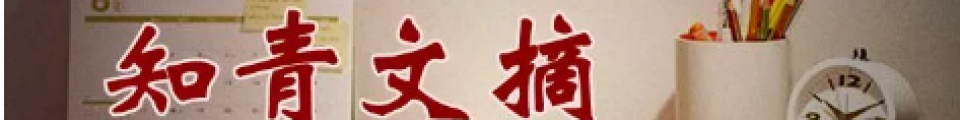故乡安铺,位于雷州半岛平原的西北角,那里河渠纵横,田连阡陌,低坡无岭。因而思乡时,只有一泓浓浓淡淡的水,常在记忆中。
此刻,我的目光会止于几只低飞的白鹭或更新了多年的文笔塔,其实塔后是十多华里的堤坝,也是十多华里的秀美画廊。
每每听母亲讲述这段经历,我总是暗自惊叹:一名城里长大的弱质女子,一个从小倍受呵护的独生女儿,是怎样在陌生的乡村里,独自挑起了劳作和生活的担子!
这种景况自父亲转安铺中学任教为止。那时候,教师像一群不按季节飞翔的候鸟,常不知何时在何地栖息多久。或像河溪里的浮萍,流动是常态,有时也会在拐弯处搁浅。
我长大后,听家姐说,我出生那年,是家人最快乐的日子,除了家添男丁,母亲还调往圩镇,一家人得以团聚。
父亲并未没有停止“漂泊”,不久,他飘到对岸,后来,回到他的故乡,再后,他……
母亲并没有随同,或留恋太完美的安铺,或因为弟妹接续现世,“翅膀”压得太重吧,虽然时常听母亲低声哼着那首歌:
这首歌名叫《送别》。母亲女红精巧,有绘画的天赋,读师范时,因讨厌美术老师,却选修了音乐。但嗓音不美,我很少听她唱过别的歌。
我趴在母亲的背上,入住了这座名镇。在这里学走学话、启蒙识字,十数年把它住成了故乡,把自己长成了安铺仔。虽然家还不停地挪动,但仅限于镇内。
早年,学校多设于庙宇,教师们的散租在百姓的房子。我们在安铺第一个居点,租住在一个名叫三婆的家。虽然是一间简陋的瓦房,但在镇子唯一的公园里。门前花树亭阁、流溪池塘,现在所谓的五星级的家也不过如此。
如今亭阁依然,池塘依然,坡上绿荫依然。还添了若许仿古建筑,池塘换上几条新桥。只觉水不动,桥略宽,少了咋日小桥流水的韵味。
当然,我们更多时候住在校园。我们跟随父母,几乎住遍了当年小镇几间中、小学及分校校园。
母亲在中大街小学任教时间很短,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校门开在小巷,也是著名的十八阶青石板的旁边。走出小巷,右下穿过一条小桥,便是西街了。但现在桥没有了,因为桥下那条穿起古镇的溪流也没有了。
一山指山沟棚,一个杂树丛生的浅坡。三溪,是小镇自南往北流向九洲江的东溪、西溪和瓦窑溪。东溪从龙潭流出,在杂树乱枝的遮掩下,在屋宇和石缝间迂回曲折,经中山公园侧畔汇入九洲江。瓦窑溪少去,记不起它的样子。
与中大街小学为邻的西溪,源于山沟棚,家乡人亦叫它咸鱼沟仔。大约因是它流经咸鱼行过,在校园搁楼可眺望它汇入江河的鳞鳞波纹。
“皇帝女”不愁嫁啊!那个年代,广州太远,香港不敢。要不几城的次序要重排了。
听了这首歌谣,身为安铺仔的我,有点气不平了。我们很差吗?安铺仔大致可分为两类,文人和武人。也有文武双全的,那只是一小撮。
小镇文人荟萃点很多,聚人甚众,均艺高八斗,无论表演或奏乐,无论字画或棋艺,都有出色的代表。如.西街罗铁珊的写大字传奇,流行街市至今。
某年某月,雷北(州)县胜利公社恢复旧称,中学的额匾也须重题。小镇能担当此大任的只有罗铁珊。于是,小镇最高学府的最高层领导亲临罗府,经一般动员,始得罗先生首肯。
择日,校方拂扫中堂,把铺在地上的二十八张《南方日报》,粘贴成七大块,把一打墨汁,倒进洗脸盆里,并备一筐糠头灰。当然还在旁边放一张课桌,桌上盛着一壶冲好的绿茶……
冇识字也能作诗的叫老全仔,堪称安铺的“李有才板话”。无论颂扬新风,或针砭时弊,都有长篇传世。那些顺溜的诗句,当年三岁的孩童都会诵传:
长长的临街骑楼,也有多群徒弟在扎马练武。不过,多厉害高手也无非出自猪笠进伯或撑渡生哥的门下。进伯曾经任县的武协主席,厉害吧!
当年,家姐觉得我身子孱弱,就请她一位食过”夜粥”的同学来教我功夫。说:就学几手散手,别人不敢欺负。但我只学了几晚,扎马虚松松的,就罢了。家里冇夜粥食,那能练成硬桥硬马呢!
事实上,故乡的语言异常丰富,特别是形容词,表示颜色:白膝膝、黑咳咳、青悲悲;表示味道:香喷喷、甜糖糖、酸呱呱;表示体态则有:肥藤藤、瘦蚊蚊、高寮寮等等……
故乡为悠久历史商贾集镇,汇杂了白话、黎话、哎话、海潦话等多种生活语言,其中许多,生动活泼、精致细微以至只能言传而无法书写。
九洲江流近故乡,在高墩处便分支两河,浩浩荡荡奔往北部湾,洪流中那块冲积小平原,故乡人叫它为围田。那里水渠纵横,鱼米丰盛,是最好做食的安铺近郊。它与南郊、故乡人称之“坡地”的几条自然村合抱着小镇。
啊!只有美美的故乡水才滋养出如此生动、奇特的品质。水的灵气、水源的充沛、水运的便捷,和因此伴生的周边村落的物丰民阜,成就了故乡的兴起与繁荣。
当年,为躲避武斗“战火”,我家在牛皮塘村住一晚。早上,在母亲的同事朱老师家里,品尝过香甜的粟米粥。
每个黄昏,趁着余晖,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奎哥还有几个父亲得意的弟子,到河沟里玩水摸鱼。那水刚及胸口,冷暖宜人。但有一次我未踩稳,身子一歪,水淹过头,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父亲忙扑过来,把我扶起。
母亲调到南街小学后,家里开始卖掉父亲的书。也许书的内容太深,人们分不清是香花还是毒草;当然物质困难时期,废品站的钱也是钱。且卖书是最实际的减负,南小教工宿舍太窄,且须每学年搬家一次。
操场西面,还有两间民居般的低矮瓦房,其中一间是一(2)班教室,那是我开蒙的地方。
在这窄小的校园里,我也结识了一班好伙伴,近一个花甲回头,他们还是知己朋友,细细思量,他们竟然是当年的男性班干的全部。大队委阿伟、班长兼中队长水泰、小队长学儒、水庆。我,不好意思,臂挂两横中队委。
这些班干们和我当年在校内或邻里结交的,如朝明、里均、瑞源、季成、一坚等多位发小,在往后的生涯中的某一段或全段,还是社会和人群中的中坚,即使在人生的最低谷,还那么顽强和发奋。
好伙伴中也有四年级才入队的”落后分子”宽到。当年,班里有歌谣唱他的:
宽到个子小,常坐头排靠墙,头顶上挂着报纸。亦如此,老师对他视而不见。不过,宽到赶超班干从不停步。至今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已回家含饴弄孙,他的名字还写在社区的先锋榜上。
我读三年级时,学校迁至油行尾,油行那些窄长的、还散发淡淡油垢味的仓库为教师的办公室和宿舍。不过,已有明亮的教室,和宽敞的校园。
那时候,虽然没有泳池,但安铺河边、高敦水坝、水袋、龙潭…,处处可玩水可学泳啊。
水袋,是九洲江截流成青年运河后,一支流返馈故乡,在东郊建成的小型储水库。不久,我在水袋里无师自通,学会了狗爬、扑蝶、撑昂船(仰泳)等游水招式。因为胆小,至今未能学成高台插水和抽水钩。
在清晨或傍晚,在水袋或河边,我都看过“水鬼”们的精湛的表演。他们与奥赛的那些镜头只差跳台不同。这让我羡慕到仿效,结果在水面上,“搭”(摔)得肚皮发红,只好放弃了。
虽然,国家梦之队没见安铺仔身影,但有几位奥运跳水冠军,的确是故乡人教的。那位乡友是我住豆仔行的钟姓邻居。
安铺可戏水的水域,只有龙潭我未泳过。龙潭,单是听名字就有三分怯意,龙潭虎穴,凶险之处。
十岁那年,我和同学探访龙潭一次。虽然从小听过龙潭的传说并有敬畏之心,但我们也学了这课书:
会背那么豪气的诗句的我们,不敢去龙潭戏水吗?当然得背着母亲。
东溪,在汇入九洲江的途中,有两口井,因地势一深一浅,但均蕴藏故乡最甘甜的水,到底是龙源仙泉啊。
不久,母亲调到中心小校任教,我们也随迁住入原同文书院的古老房子。由此,我们一家也饮用上东溪边最深的那口井水。
那口水饮得有点艰辛,一担水近八十斤。然后从井头至学校数百米都是陡削的上坡路。沉重的担子,一步步,不歇肩,不倾洒。这大约是我最早承受的生活担子。
但那水性的确晶莹、纯洁、甜润。然而,故乡的哪一滴露珠,哪一束细流,哪一簇浪花,不是上善之水呢!